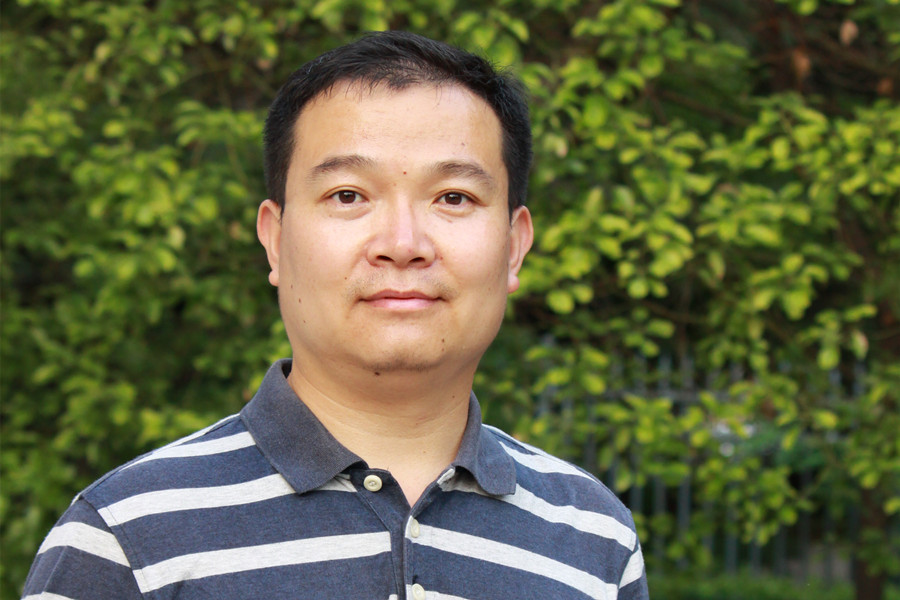
作者简介:穆海亮,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戏剧研究。在《戏剧艺术》《戏剧》《戏曲艺术》《新文学史料》等期刊发表论文60余篇,曾获第四届“中国戏剧奖·理论评论奖”等。
一
作为孤岛时期存在时间最长、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话剧团体,以于伶为主要负责人的上海剧艺社(简称“上剧”)堪称孤岛剧运的中流砥柱。黄佐临是中国话剧史公认的戏剧大师,不仅以其精湛的导演艺术打造了一个个舞台经典,而且还以对“写意戏剧观”的倡导在话剧史上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黄佐临于1939年参加“上剧”,按理说,二者的合作应该是强强联手、珠联璧合。然而,事实似乎并非如此。1941年9月,黄佐临与吴仞之、石挥、英子、张伐、韩非、黄宗江、史原、胡导、梅邨、严俊等人突然宣布脱离“上剧”,与姚克、周剑云一起,另组上海职业剧团(简称“上职”),这就形成了“上剧”历史上重要的“分家”事件。
“分家”事件的发生极为突然,此前没有任何征兆。就在1941年8月,适逢“上剧”成立三周年纪念之际,“上剧”还隆重推出黄佐临导演的《边城故事》作为纪念剧目,一直演到8月27日。“上剧”当局对该剧极为重视,还在演出广告上别出新裁,以富有煽动性和悬念性的语言逐日介绍剧中人物和演员,这在“上剧”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做法。8月5日,“上剧”为庆祝建社三周年在辣斐举行游艺会,全体演员参与颇具趣味性的演出。后来跟随黄佐临离开的演员们及黄佐临的妻子丹尼全都登场献艺,黄佐临还亲自登台,为严俊等人的平剧《法门寺》跑龙套。整个游艺会喜气洋洋、情意浓浓。谁也不会想到,仅仅在一个月之后,就发生了令所有人感到意外的“分家”事件。
客观说来,“分家”事件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削弱了“上剧”的实力,对其艺术活动产生了一些影响。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上剧”原本定于在《牛郎织女传》之后上演的《恨海情血》《苦恋》《天外》等剧均无法如期上演,“上剧”只得临时翻演老戏《女子公寓》以应急。该剧为“上剧”保留剧目,不需排练即可登台;而黄佐临拉走了“上剧”男演员中的骨干成员,“上剧”搬演这出“女人戏”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危急时刻,阿英主持的新艺剧社(简称“新艺”)伸出援手,协助“上剧”将“新艺”演过的《海国英雄》搬上辣斐的舞台,这才使得“上剧”的演出没有因为“分家”事件的影响而中断。“分家”事件对“上剧”的影响也并非完全致命。在经过短暂的过渡期后,“上剧”立即招收新社员,并于10月9日起推出新剧《妙峰山》,自11月6日起推出新剧《北京人》,依然保持了较高的艺术水准。要不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上剧”的演出活动仍会延续下去。
关于这次“分家”事件,当时的舆论普遍对“上剧”表示了同情和惋惜,将之视为对“上剧”的损害,并将之归因于剧运内部长期存在的人事纠葛,呼吁加强剧人的团结以促进剧运的发展。《神州日报》“神皋杂俎”副刊先后刊发《给剧艺社》《关于剧艺社》二文,前者对“上剧”的“分家”表达了忧虑之情,希望“上剧”能够团结起来继续奋进;后者在对“上剧”的分家表示惋惜的同时,认为这可能会对“上剧”造成一时的困难,但不会对整个剧运产生太大影响,希望剧人们能够注重思想,提高觉悟,真正为剧运而努力,不要为了名利或人事纠纷影响剧运前途。自然,其中也有一些争论。如《正言报》“剧坛”副刊登出的《孤岛话剧运动的阻力》一文,虽用词含混,没有明指,但从其发表时间、当时剧运的实际情形以及字里行间流露的意味来看,很可能是针对黄佐临脱离“上剧”另组“上职”一事而发的。本文直接以“分裂”来形容这次事件:“这种自我的分裂,好听一点说是剧运力量的扩展,但实际上也可以说是剧运力量的分化。我相信,将来总会有一天各剧社都感到营业的不振,剧本的不够分配,导演人才的缺少和演员阵容的不够坚强。”本文很快引起了回应,署名“赵莽”者《谁是孤岛剧运的阻力?》一文就是对之所做的反驳。赵文别有深意地说:“一个有历史,有地位,有优良工作者的剧团,为什么大家都不愿意为它永久努力?‘阻力’的焦点就在这里。剧团里产生了一批分化作用者,目的不是做艺术工作,而是用某种‘作用’去通过艺术,造成分裂的局面。”赵文认为,孤岛多增加一个新的剧团,只能是对剧运的促进而不是分裂,“难道孤岛的剧运只有一个团体就能推动,增多了新的活动者便能产生出阻碍而陷于停顿?”双方的争论显然都带些火气,所以《正言报》编辑马上加了“编者按”,制止争论继续下去。战后,于伶返沪重建“上剧”,连续推出《戏剧春秋》《两小无猜》两戏,均卖座平平,亏损颇多。危急关头,恰是黄佐临鼎力相助,以圆熟的导演技巧成功地将陈白尘《升官图》搬上舞台,连演四个月,弥补了“上剧”的亏空。当时有报道称,黄佐临私下语友人曰:“我已将功赎罪,不再是剧艺社之‘叛徒’矣。”黄佐临是否真的这样说过我们自然无从知晓,但由此可知,舆论还是认为黄佐临等人应该对“分家”事件承担责任。
“分家”事件发生时,于伶早已离沪赴港,但他对于自己付出过巨大心血的“上剧”饱含深情,所以也对这次“分家”事件感到愤怒。在10月30日写给田汉和欧阳予倩的信中,于伶如是说:“上海剧艺社为弟、健吾、仲彝、松青(剧场艺术编者即李伯龙)、徐渠、端钧、吴天诸兄四年余之心血,近受姚克、黄作霖、周剑云等之阴谋破坏,几致解体。幸干部团结,仅被控拉演员九人。姚周等另立一‘非常有钱’之上海职业剧团,上海剧艺社同人外受种种恶势力之轧压,内遭同路人之暗算,艰苦益甚!”桂林的田汉等人都对“上剧”表示同情,香港的夏衍也答应专为“上剧”编一剧本以示帮扶。作为另一方当事人的黄佐临等人很少对此事发表直接看法,似乎在有意回避。直到晚年,吴铭撰文旧事重提,对黄佐临等人颇有微词,称他们脱离“上剧”,“致使剧艺社的地下党组织一时陷于十分困难的境地,给国民党反共分子和别有用心的阴谋破坏者以可乘之机,做出了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甚至称石挥“政治背景也十分可疑”。吴文这种上纲上线的行文方式,引起了黄佐临的极大不满,他迅即撰文进行义正词严的辩驳。黄佐临认为,历史已经证明,他们另组“上职”促进了而非削弱了剧运的发展,而石挥的问题早已有了定论,不容再泼污水。文章结尾处,黄佐临不无悲愤地写道:“‘上职’这段历史,五十年来,我一直为此挨骂,在私人场合骂,在公开场合骂,我一直保持沉默,付之一笑。但现在既然公开见之于文字,我当然有替自己辩白的权利,把是非曲直,公之于众。”从黄佐临的表述中,我们不难体味到一种长期隐忍造成的压抑感和不吐不快的激愤,同时黄佐临自己也承认当时脱离“上剧”的方式和时机没有把握好,这似乎也曾让他有一丝隐隐的愧疚。那么,黄佐临等人到底为何要脱离上海剧艺社呢?
二
首先,孤岛后期的剧运形势为“上职”的出现提供了外在条件。抗战爆发后,沪上大批剧人纷纷奔赴内地,滞留上海的剧人力量相对薄弱。再加上孤岛初期政治形势尚不明朗,能否以及如何开展话剧运动,都前途未卜,孤岛剧人只能小心翼翼地开展试探性的活动。先是组织青鸟剧社,但不久即因内部纠纷及经济原因宣布解散。随之成立的晓风剧团和上海艺术剧院也未能坚持太久,前者因经济来源不明、涉嫌日伪背景而解散;后者则因租界当局拒绝登记而被迫终止。孤岛前期,戏剧运动一片沉寂。1938年7月17日,上海剧艺社正式成立。先是举行不定期的大剧场公演,又进行过十二期星期小剧场实验演出,自1939年8月6日首演《夜上海》起,“上剧”开始了长期职业公演,直到孤岛沦陷。正是“上剧”的努力和坚持,打破了孤岛剧运的冰封局面,以政治意义强、社会价值广、艺术水平高的舞台演出锻造了一批迅速成长的优秀剧人,吸引和培养了大量市民观众,同时也促进了业余戏剧交谊社等业余演剧的蓬勃开展,并带动了中国旅行剧团、天风剧社等大剧场职业公演的持续展开。剧运星火遂成燎原之势。孤岛后期,无论从剧人的艺术修养、剧团的剧目建设、演剧水平还是从观众储备、市场需求等各方面来看,都已完全具备了成立更多剧团、开展更多演出的客观条件。黄佐临成立“上职”,自1941年双十节在卡尔登开演《蜕变》,继而推出《阿Q正传》《凤娃》二剧,加上原有的“中旅”在天宫、“天风”在璇宫、“上剧”在辣斐的演出,孤岛同时有四家剧院在上演话剧,而且观众踊跃,卖座上佳。这说明孤岛后期戏剧运动的蓬勃发展为成立新的剧团奠定了必要的基础。“上职”在此时成立,可谓顺势而为。
作为孤岛剧运的绝对中坚,“上剧”集中了数量过多的戏剧人才。编剧方面,不仅有于伶、阿英、顾仲彝、李健吾等新作频出,而且不断有内地剧作家(曹禺、夏衍、张骏祥、吴祖光等)寄来佳构;导演方面,上海剧坛四大导演中有三人(朱端钧、吴仞之、黄佐临)为“上剧”导戏,更有吴天、吴琛、洪谟等基本导演全职坚守;舞美方面,池宁、徐渠都是行家里手;演员方面,原有的夏霞、蓝兰、柏李、徐立等均是经验丰富,新生力量石挥、黄宗江、韩非、张伐等也是业务精湛。真可谓人才济济,实力非凡。但过多戏剧人才集中于“上剧”必然导致一些演职人员无戏可演,这不能不说是人才的浪费。实际上,石挥、英子等“上剧”的后起之秀虽然已分别在《正气歌》《边城故事》等剧中担任了主要角色,受到剧社当局越来越多的重视,但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在“上剧”演戏最多、地位最高的还是最初即加入进来的“元老”们,这自然会让这些后来者心有不服。更何况,如石挥、韩非等个个身手不凡,都是可以独挑大梁的实力演员,怎会甘于久居人下?所以,一方面是孤岛剧运迫切呼唤着新的戏剧力量的涌现,一方面是“上剧”优秀剧人过分集中导致的资源浪费,两相作用,遂使黄佐临等人萌生了另组剧团的想法。而跟随黄佐临一起离开的演员,清一色都是“上剧”后期陆续招进来的,而“上剧”最初的“元老”们都不为所动。“上职”成立后,“上剧”并未因此停滞下来,双方还能气势昂扬地唱起对台戏,这也从侧面说明“上剧”确实具备了在两个剧场同时开演的雄厚实力。
黄佐临等脱离“上剧”,恐怕还有一个经济方面的原因不能不提。据胡导先生回忆,“上剧”的导演分为基本导演和特约导演两类。基本导演如吴天、吴琛、洪谟等,除承担导演工作外还负责剧社的行政事务,其收入除了百分之三的导演税,还从剧社按月领取基本工资。而特邀导演如黄佐临、朱端钧、吴仞之等,导演税是其在“上剧”的唯一收入,而没有基本工资。在人才济济的“上剧”,当然不能保证每位导演都有戏可导,这必然会让这些特约导演经常处于赋闲状态,从而影响其经济收入。对此,朱端钧或许并不在意,因为他原本就是出于对戏剧的爱好和对剧界同仁(尤其是于伶)的友情来参与导演的,他同时还在经营着一个祖传布庄以养家糊口。吴仞之原本在中学做数学老师,后来为了戏剧辞去教职,一心一意做导演,长时间的赋闲自然会影响其生活来源,所以他还常为业余剧团导戏,并为“天风”导演方言版《上海屋檐下》。黄佐临家境富足,也在大学兼课,经济上或许没有问题,但他来上海就是要全心全意搞戏的,在“上剧”的这种“兼职”岗位,用他自己的话说,使他仅仅处于类似“客卿”的位置,自然让他难以满意。在这种情况下,一有周剑云、姚克以“非常有钱”之新剧团相号召,黄佐临、吴仞之等人脱离“上剧”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值得一提的是,跟随黄佐临脱离“上剧”的演员们大都参加了他为“上剧”导演的几部戏的演出,这最直接的创作实践让他们对黄佐临高超的导演艺术心悦诚服,感觉跟随黄佐临可以在艺术上获得更大的发展。黄佐临的巨大号召力形成了一个有一定凝聚力的艺术共同体,从“上剧”到“上职”,再到“苦干”,黄佐临始终能够团结一批年青剧人共同奋斗,这就是艺术共同体的向心力使然。
三
如果说后期孤岛的剧运形势和“上剧”内部的分工差别是导致黄佐临脱离“上剧”的外部诱因的话,那么黄佐临与“上剧”在艺术理想、艺术观念方面的根本差异才是“分家”事件发生的内在缘由。
上海剧艺社是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戏剧团体,于伶本人就是地下文委的委员,他是在接受了明确任务的情形下组织“上剧”的。其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团结孤岛剧人,开展进步剧运,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尽量争取上演意识积极、有利于巩固孤岛人民“心防”的剧目。因此,上演剧目的政治意义是“上剧”必须坚持的一个原则。另一方面,孤岛毕竟不同于大后方,剧运的开展只有借助一定的保护性外力才能坚持下去,一旦由于活动激进而触犯当局,就连剧社本身也无法立足。所以“上剧”的策略就是首先要争取生存和演出,然后在演出中宣传永不屈服、抗战到底的思想意识。事实证明,“上剧”的策略收到了效果。比如以中法联谊会为依托,挂半个洋商牌子以自保,尽量与租界当局维持良好的关系,请做过杭州市长的国民党员赵志游担任挂名社长,等等,都是为求得立足的资本。在剧目选择方面,既有《人之初》《爱与死的搏斗》《祖国》这样暗含深意的法国名剧,也有《明末遗恨》《大明英烈传》《梁红玉》这样以古喻今的主战题材,还有《夜上海》《愁城记》这类“表现上海”的现实佳作。这些作品,无一处直接写到抗战,又无一处不与抗战相关。这些策略的实施,既保证了安身立命的政治安全,又实现了思想宣传的政治意图。“上剧”的这些特点,在孤岛时期有其毋庸置疑的合理性与必要价值。
黄佐临两次留学研习戏剧,在抗战全面爆发后回国也是为了一心一意开展戏剧事业。相对而言,他对政治比较隔膜,甚至有些反感。1938年,曹禺的一纸聘书让黄佐临夫妇满怀热情地奔赴重庆国立剧专,希望能在艺术事业上大展宏图。但是这个官办剧校的官僚作风、政治习气令黄佐临十分不满,连想排夏衍《上海屋檐下》的愿望都被他留英的“同学”张道藩拒绝,这让黄佐临感到抱负难以实现。遂借赴天津奔丧之机,滞留于上海孤岛。人生地不熟的他拿着曹禺的一张名片找到李健吾,参加了“上剧”的导演工作。然而,踌躇满志的黄佐临很快就发现“上剧”并非实现其艺术理想的最佳平台。由于“上剧”肩负的政治使命和独特的政治背景,它在很大程度上继承和发扬了左翼剧运的作风,对黄佐临这样从未与左翼戏剧发生关系的人,并未给予充分的创作空间。近两年时间,黄佐临只为“上剧”导演了三个戏,分别是张骏祥的《小城故事》《边城故事》,以及朱端钧改译的《圆谎记》。尽管手法娴熟,精彩叠现,但其“思想意识”并不被人看好,尤其是《小城故事》《圆谎记》被视为与孤岛现实相隔膜。而导演的另外两出短剧《白取乐》《求婚》分别只是作为《鸳鸯劫》和《镀金》的“加演戏”而上演的。这难免会让黄佐临有壮志难酬之感,所谓“客卿”之慨大概由是生焉。
艺术理想或观念方面的错位,既使“上剧”没有给黄佐临以施展抱负的广阔舞台,也使黄佐临对“上剧”的某些业余做派感到不满。黄佐临希望的是像莫斯科艺术剧院那样的正规化、专业化演剧,他认为“上剧”具备这样的潜力,却不具备这样的雄心,种种业余气息阻碍着它的进一步发展。这些业余气息“上剧”自始至终未能完全摆脱,尤其在于伶离开后还越发彰显出来。首先是人事纠纷不断。于伶刚走,“上剧”原总务主任吴琛、宣传主任毛羽辞职;接着由李健吾任演出部长,李伯龙任总务部长,但二李的意见亦不为社员所理解,不久即悄然辞退;接着由顾仲彝出任剧务部兼总务部,吴崇文任宣传部长,“吴连日分往各报馆拜客,一如‘京角儿’作风”。再加上赵志游这样一个官僚出身的社长,当选工部局华董还要“上剧”全体社员赶去为之庆贺。凡此种种,都让人感觉“上剧”似乎难以成为一片艺术净土。其次,剧团组织方面的业余作风必然影响舞台演出的整一性。演员排演不敬业,吴永刚应邀为“上剧”导演《花溅泪》时,就曾因为多次排演演员始终未能到齐而忍不住在报纸上发了一通牢骚。忘词、台词生疏、念错别字甚至舞台上“吃豆腐”的现象时有发生,由于个人原因临时找人代戏的情况更是屡见不鲜,胡导一人就曾为多人代戏,石挥、黄宗江在“上剧”的演出生涯也是从代戏开始的。《家》卖座最好的时期,居然发生主要演员集体请假赴兰心欣赏《洪宣娇》,所饰角色全部找人代戏的情况。物质方面的客观限制应该给予充分的理解,可人力方面的不够投入就值得商榷了。尽管我们必须高度评价“上剧”为孤岛剧运做出的巨大贡献,但我们也不能回避的是,“上剧”原本可以做得更好。此外,“上剧”的某些策略表现得对艺术不够执着。比如,在剧目选择上,“上剧”往往会为了“政治安全”或“现实意义”而忽略其“艺术价值”。曹禺的《蜕变》专门寄给“上剧”,但由于租界当局认为“不妥”,“上剧”就为了维持现状而放弃,该剧被压一年多未能上演。这在黄佐临看来,未免过于谨慎了。曹禺根据高尔斯华绥原作改编的《争强》,本来已由黄佐临排演成熟,连广告也提前几天就打了出来,最终却临时决定弃演,原因是“上剧”内部认为该剧的思想取向与孤岛形势多有不合。其实黄佐临对《争强》极为赞赏,早在南开首演该剧时,黄佐临就在《大公报》写了一篇观感,极为内行地比较了南开演出与高氏原作之间的差异,令曹禺十分佩服,遂登门造访,两人成为挚友。这次《争强》的最终弃演让黄佐临颇感失望。再如,1941年8月,“上剧”与辣斐合同到期,卡尔登主动与“上剧”洽谈合作事宜。卡尔登位置更好,剧场环境更佳,但提出的合作条件也比辣斐更高。“上剧”内部经过激烈争论,还是保守派占据上风:宁可在辣斐继续维持现状,也不愿为了话剧艺术的前途而到卡尔登冒险。
黄佐临对“上剧”拒绝卡尔登一事的态度我们不得而知,但从他组建“上职”后采取的一系列举措来看,似乎都有所针对。他的剧团取名“上海职业剧团”,旗帜鲜明地与一切业余作风划清界限;打炮戏选择《蜕变》,意味着向公众表明:只要戏好,“上职”不惧任何政治风险;场地选择卡尔登,同样暗含着宣示的意味:为了戏剧运动,“上职”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四
从某种意义上说,《争强》的弃演或许可视为黄佐临与“上剧”之间艺术观念之错位的缩影。在1941年的《中美日报》“艺林”副刊第184期上,有一条关于《争强》弃演的简短消息,并特意加了“编者按”,在今天看来,真是意味深长:“吾人希望剧艺社能保持过去的光荣,再接再厉地战斗下去。‘人事问题’应即从速克服,‘艺术至上主义’是剧运的一条歧路,也是走不得的,及早回头吧!”这段话的表述在逻辑上并不太清晰,但至少给我们提供了如下信息:当时的舆论界欣赏上海剧艺社向来的“战斗”传统而拒斥所谓的“艺术至上主义”。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争强》绝不是“艺术至上主义”的作品,希望上演《争强》的黄佐临也绝不是所谓的“艺术至上主义”者,他只不过在“政治意义”和“艺术价值”之间,将后者放在了更为显要的位置而已。
既然如此,为什么在“上剧”“分家”事件中黄佐临长期处于受批评的一方呢?难道仅仅是因为“上剧”似乎处于“受害者”一方就占据道德上的优势么?这恐怕必须要还原到孤岛的特殊语境、乃至中国话剧发展的独特历程中去考量。实际上,黄佐临与当时滋养着中国话剧的特殊土壤存在着些许错位,因为与政治的纠结,和对剧作的社会意义的强调,几乎是中国话剧与生俱来的命运,更何况是在孤岛,是在继承了左翼剧运传统的上海剧艺社。在孤岛那样国将不国的险恶环境下,“上剧”把政治诉求作为演剧艺术的首要参考,把战斗精神作为支持剧运发展的前进动力,这种坚贞而清醒的立场应该得到我们深切的理解与同情。
但历史的吊诡之处也恰恰在此呈现:中国话剧的发展始终不能与政治撇清关系,它的辉煌偶尔由政治性造就,它的困顿也往往是源于政治性的束缚。就上海剧艺社来说,正是鲜明的政治意识在很大程度上鼓舞着孤岛剧人奋力拼搏,吸引着大量观众涌进剧场;同时也是这种对政治环境的妥协、对政治势力的依附、对政治理想的追求、对政治观念的坚守,使得“上剧”未能在职业化、专业化、正规化的道路上更进一步,自身遗存的种种业余气息限制了它在艺术创作上的更大成就。而追求艺术自主性的黄佐临另组“上职”,虽然在客观上暂时削弱了“上剧”的力量,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上职”进一步扩大了话剧的影响,发挥了话剧的社会作用,为剧运的整体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历史没有给“上剧”提供克服自身发展瓶颈、抵达戏剧艺术巅峰的机会,也没有给“上职”提供发掘艺术潜力、实现自我提升的舞台;但历史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黄佐临、石挥等人脱离“上剧”之后,在话剧艺术上取得了更多的建树,黄佐临后来组建的同人合作、自立自主、不依赖任何政治势力的“苦干剧团”成为中国现代话剧史上演剧水平最高的剧团之一,石挥也在沦陷时期成为上海的“话剧皇帝”。黄佐临的艺术理想与上海剧艺社的艺术观念之间,到底谁能够代表中国话剧发展的正途?其中的是非功过,恐怕绝非一两句话所能说得清了。
文章原发:《戏剧文学》201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