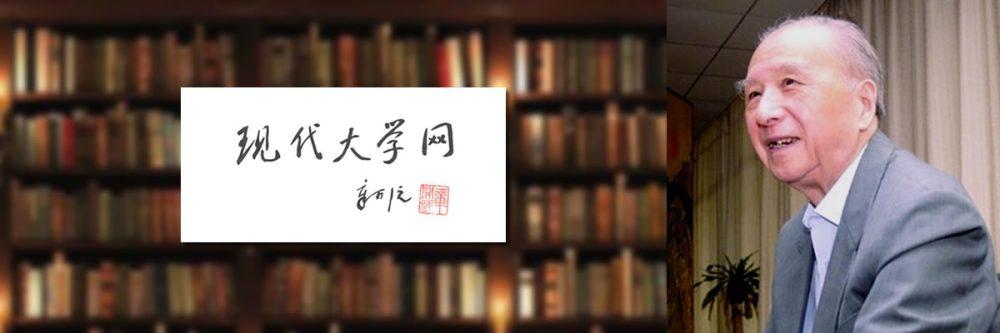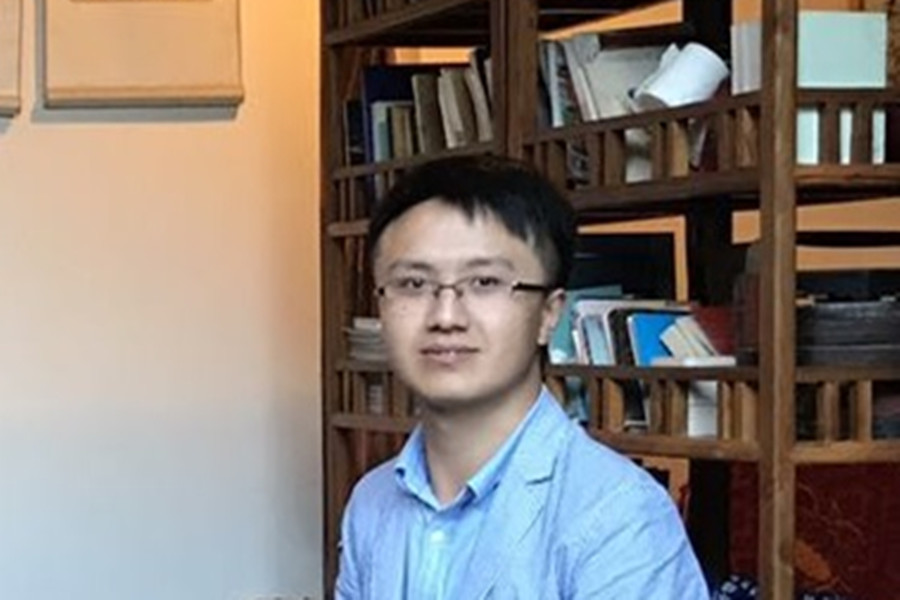
作者简介:白文昌,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深秋,东陆园的银杏叶又黄了,金灿灿的叶子在风中偏偏飘落,让人浮想联翩。无论是清晨亦或是黄昏,每天,远近而来的游客蜂拥着挤入人潮滚滚的银杏大道,驻足停留,拍照留念,像是在朝圣一般。平日树枝上乱窜的小松鼠也被喧嚣的人群吓得不见了踪影。
图书馆的钟声悠扬,古老的会泽院静静地矗立在南国春城的闹市中,诉说着东陆园近百年经历的风霜雪雨。然而,来来往往的游人(甚至东陆园的师生)中,却很少有人知道,也极少有人还能想起那个种植了这些银杏树的老校工,他的名字叫武文忠。半个多世纪前,正是这个老校工种植并艰辛地挑水浇灌了这些今天傲然挺立的银杏树。如果没有他,点缀东陆园春夏秋冬的,又会是怎样的风景?导师董云川先生说:“大学有消息,却没了故事”。今天,与武文忠的故事一样,那些曾经发生在各个大学校园里,感染、激励过一代又一代学人的大学故事正逐渐被人们遗忘,落魄地消失、湮没在了历史的风尘里。东陆园中,我们再难寻觅到类似熊庆来、费孝通、刘文典的故事——整个中国大陆的高等教育在迷失!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先辈们曾经抛头颅洒热血奔忙追寻的那些东西,最后都去了哪里?今天,当我们再次回望那个烽火与硝烟弥漫的年代之时,梅贻琦、熊庆来、费孝通、顾颉刚、刘文典等一个个伟岸的身影依然无比清晰地浮现在我们的面前……这些身处大动荡、大灾难之时代的大师们,在经历了今天人们难以想象的艰辛与悲恸之后,终于让那些被称为“黑暗的中世纪里隐隐约约闪现之星光”的“象牙塔”在神州大地上屹立起来。然而,当我们将目光聚焦在今日之“象牙塔”的时候,却悲伤地发现:在这个号称物质与精神都极其丰富的时代,能被人们称之为大师的人却寥寥无几。院墙内外高楼大厦平地拔起,学术内外课题项目像漫天飘飞的沙尘肆虐地吞噬着大学人本该潜心研究的学问……,功利而浮躁的学者越来越多,务实却快乐的学人越来越少。专家被人们戏称为“砖家”,“教授”也被人们蔑视为“叫兽”,原本情同父子(父女)的师生关系成了这个时代饱受诟病与争议的问题。
我们一面奔走呼号像是患上了“大师饥渴症”一般地企盼大师,另一面却又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个大师的背影无奈地抛下我们,迅速地远去。“卓越人才计划”、“卓越工程师计划”、“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珠峰计划”,我们热衷于搞各种各样意在造就大师的工程和计划,却一次次被撞得头破血流。大师究竟在哪里?陈平原先生说:“我们生活的时代,到底是天才辈出,还是平庸得只能在矮子里面拔高个?”没有人说得清楚。
然而,我们始终坚信的是,大学不能没有大师。一所大学的大师,就像海上的灯塔,指引着大学人的前进方向,引导着他们在偏离了人生航向时懂得迷途知返。梅贻琦先生说,“大学者,非大楼也,乃大师之谓也。”陈平原先生又说,“大学精神之所寄,在于教师的树立楷模与学子的自谋修养。对于大学来说,大师之所以重要,不止因为他们拥有渊博的学识、超群的智慧,更因为他们的人格和修养可以成为学子们追慕的目标。”他们的人格,他们的风范,以及他们的学术趣味,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大学人,学人们互相感染,而后又将他们的故事接着传下去。在故事的流传中,大学也就形成了自己的发展脉络,塑造了自己的精神和品格。这种精神和品格,正是大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力量与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