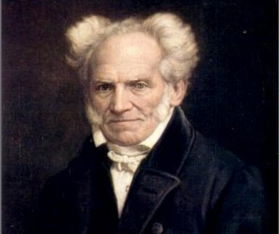
日常生活里,一旦没有激情来刺激,便会令人感到沉闷厌烦,枯燥乏味,有了激情,生活又很快变得痛苦不堪。惟有那些因自然赋予了超凡理智的人,才是幸福的人,因为这能够使他们过理智的生活,过无痛苦的趣味横生的生活。仅仅只有闲暇自身,即只有意志的作用,而无理智,那是很不够的,必须有实在的超人的力量,要免于意志的作用而求助于理智。正如塞涅卡所说:无知者的闲暇莫过于死亡,等于生存的坟墓。由于心灵的生活随着实在的能力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心灵的生活能够无止境地展开。心灵的生活不仅能抵御烦恼,而且能够防止烦恼的有害影响。它使我们免交坏朋友,避开许多危险、灾难以及奢侈浪费,而那些把自己的幸福完全建立在外部世界的人,则不可避免地要遇到这一切。如我的哲学虽然从来没有给我赢得一个小钱,但它却为我节省了许多开销。
凡夫俗子们把他们的身外之物当做生活幸福的根据,如财产、地位、妻室儿女、朋友、社交,以及诸如此类的一切,所以,一旦他们失去了这些,或者一旦这些使他失望,那么,他的幸福的基础便全面崩溃了。换言之,他的重心并不在他自身。而因为各种愿望和奇怪的想法在不断地变化着,如若他是一位有资产的人,那么他的重心有时是他的乡间宅第,有时则是买马,或宴请友人,或旅行——简单地说,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这也就是他从他的身外之物寻找快乐的原因。在论及相反情况以前,我们先比较—下在两个极端之中的这一类人,这种人并没有杰出的精神能力,但其理智又多少比一般人要多一些。他对艺术的爱好只限于粗浅的涉猎,或者只对某个科学的分支兴趣——如植物学,或物理学、天文学、历史,并能在这种研究中找到极大的乐趣朝一日,那些导致幸福的外在推动力一旦枯竭,或者不再能够满足他,他便会靠这研究来取悦于他自己。这样的人,可以说,其重心已经部分地存在于他自身之中但这种对于艺术的一知半解的爱好与创造性的活动迥然有别;对科学的业余研究易流于浅疏,而且不可能触及问题的实质。人不应当完全把自己投身到这样的追上来,或者让这些追求完全充满了整个的生活,以至于对其他任何事物都失去了兴趣。惟有最高的理智能力,即我们称其为天资的东西,无论它把生活看做是诗的主题,还是看做哲学的主题,它要研究所有的时代和一切存在,并力图表达它关于世界的独特的概念。所以,对天才来说,最为急需的乃是无任何干扰的职业、他自己的 想及其作品;他乐于孤寂,闲暇给他愉快,而其余一切都是不必要的,甚至那不啻是些负担而已。
惟有这样的人,才可以说他的重心完全存在于他自身之中。这就说明了,这样人——他们极其稀少,无论他们的性格多么优秀,他们都不会对朋友、家庭或总之一般说来的公众,表现出过多的热情和兴趣,而其他的人则常常这样。如果他们心里,有他们自己,那么他们就不会为失去任何别的东西而沮丧。这就使得他们的性格,了孤寂的基础,由于其他人绝不会使他们感到满意,因而这种孤寂对他们越发有总的说来,他们就像本性与别人不同的人,因为他们不断地强烈地感到这种差别以他们就像外国人一样,习惯于流离转徙,浪迹天涯,对人类进行一般的思考,用我们”而非“我们”来指称人类。
所以,我们的结论是,自然赋予他以理智财富的人乃是最幸福的人,主观世界,比客观世界和我们的关系紧密得多。因为无论客观事物是什么,也只能间接地起:用,而且还必须以主观的东西为媒介。
卢西安说,灵魂富有才是惟一真正的富有,其他所有的财宝甚至会导致极大的毁灭。内心丰富的人不需要任何外在的东西,但需要与之相反的宁静和闲暇,发展和锻炼其理智的能力,即享受他的这种财富;简单地说,在他的整个一生中每时每刻,他只需要表现他自己。如果他注定要以这种特性的心灵影响整个民族那么他只有一种方式来衡量是否幸福——是否能够使其能力日臻完美并且是否完成,他的使命,其他一切都无足轻重。因此,一切时代里的最有才智的人都赋予无干扰闲暇以无限的价值,就仿佛它同人本身一样重要。亚里士多德说,幸福由闲暇构成据第欧根尼?拉尔修记载,苏格拉底称颂闲暇是我们所能拥有的最美好的东西。所以,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指出,献身于哲学的生活是最幸福的活;或者像他在《政治学》中所说的那样,无论什么能力,只要得到自由发挥,就是幸福。这和歌德在《威廉?迈斯特》中所说的也完全一致,生而有天才并且要利用这种才的人,在利用其天赋时会得到最大的幸福。
然而,普通人的命运注定难得有无干扰的闲暇,而且它并不属于人的本性,因一般人命中注定要终生为着他自己和他的家人谋求生活必需品,他为求得生存而艰难相搏,不可能有过多的智力活动。所以,一般人很快就会对无干扰的闲暇感到厌倦,如若没有一些不真实不自然的目的来占有它,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