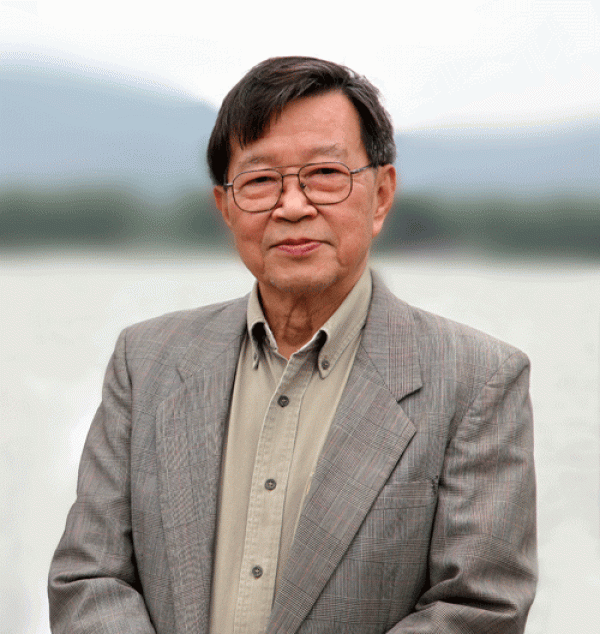朱维铮:真大师的群体意义

时近新世纪,我们的主流媒体和权威衙门,忽然争相封赏“大师”,甚至舆论愈非议而表彰更过分。个中缘由很复杂,有一点是无疑的,即将不择手段扬名立万,看做“大师”的表征。
一、“大师”的界说
上世纪中叶以后,有几十年,“学术大师”变成恶名,被指为“封资修反动权威”。直到“文革”闹得民穷财尽,这才承认“知识就是力量”。先是工艺学家和科学家,继而社会的人文的各学科的大师,都很艰辛地恢复名誉。
所谓利必有弊吧。时近新世纪,我们的主流媒体和权威衙门,忽然争相封赏“大师”,甚至舆论愈非议而表彰更过分。个中缘由很复杂,有一点是无疑的,即将不择手段扬名立万,看做“大师”的表征。
其实“大师”称谓,起初出现在汉初,并非了不起的名目。在秦始皇烧书以后,有机会听到秦博士伏胜念过烧剩的《尚书》残篇,而后跟着讲点残篇大意的山东儒生,无不称做“大师”。历经两汉三国南北朝隋唐,直到宋元明清,文化日趋普及,人们对传统的认知日趋专精,“大师”也成了对在经史诸子的特定领域真能继往开来人物的尊称。比如清末民初,梁启超在舆论界执牛耳达二十年,可谓著作等身,却没人称他为大师。所以者何?因为前有康有为、章太炎,继有王国维、陈寅恪等,都在思想文化界堪称创业垂统的大师,尽管王、陈等生前名气远不如梁。
难道大师的学识都胜过梁启超吗?不尽然,有的至今尚有争议,如马一浮。不过随着现代化日进,学术分工越来越专门,谁能在专门领域做出独特贡献,并被历史证明没有他的贡献,人文教育和科学卫生等构成的总体文明史,便如缺了一角。这样的杰特之士,当然可称大师。
谁都知道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如恩格斯所形容的,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产生了巨人的时代,“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恩格斯对引导欧洲走出中世纪的巨人即大师的讴歌,直到1925年才随着《自然辩证法》的问世而公表,被译成汉语的时间更晚。
然而,不过数年,1934年夏季,陈寅恪写作《王静安先生遗书序》,就出现了这样的说法:
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贤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
谁都知道,陈寅恪晚年曾反对当局强制研究机构学马列,却并不意味他拒绝了解马克思主义学说。相传他早年留德时读过马克思著作,又曾在瑞士听过列宁演讲。因而他的历史见解出现与马克思、恩格斯类似说法,可谓所见略同,也表明他没有“凡是敌人所是必以为非”的荒唐心态。比如关于大师巨子的历史界定,就令我每读总想起恩格斯对达·芬奇、马基雅弗利以及马丁·路德等人的赞扬,也不由得越发憎恶斯大林的假冒历史唯物主义。
因此,陈寅恪关于大师的界定,即学术实践能够继往开来,尤其善于创新,非但开拓学术新领域,而且指明学术的发展方向与方法,都是“大师”概念的题中应有之意。但他以为大师的事业 “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则未免陈义过高,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下的社会政治环境。即如他说话的时代,自称孙中山信徒的蒋介石,已在用“军政”实现所谓“训政”,以至陈寅恪要藉纪念王国维之死,呼喊学者必须保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又过二十年,他重申“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正是自己的追求,必须“以生死争之”,更说明他所说大师著作可以转移时代风气,在中国尚止于理想,迹近浪漫主义,最终被“文革”的冷酷现实所破碎。但理想的破碎不等于界定的错误。
二、现代大师的个性
主要活动时间都在上个世纪的大师们,多数人经历过由帝国、民国到共和国的时代巨变。他们都关注中国与世界的命运。他们都了解仍在中国活着的文化传统,多半都曾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历史相关度。他们未必赞同颠覆现状,却无不认同现状需要改革,乃至提倡社会政治改革。他们大多数人还有一个共同的遭际,就是生前被曲解被毁谤被诬陷,却总是恪守自己的理念,即使置身炼狱,也不放弃期盼中国现代化的追求。
近三百年的中国史表明,中国现代化的最大阻力,并非经济落后,而是明清以来的政治体制陈腐。据说清代的“康乾盛世”是传统中国的顶峰,至今仍有自诩“大师”者,指斥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是大错,宣称“告别革命”。清末官场甚嚣尘上的“开明专制论”,所谓“与上言仁政,与下言服从”,也被当做百年来“训政”在中国不绝如缕的实际理论核心。
众所周知,十四世纪以后,中国的专制主义,愈来愈以权力独裁为表征。无论帝国还是民国,元首称皇帝、总统、主席还是别的什么。唯有一人可称“今圣”。等而下之,官府无论大小,总是所谓一把手控制实权。章太炎在清末曾说中国人人都有皇帝思想,于实相虽不中,也不远。
权力至上必定导致所谓新权威主义主宰政坛。从蒋介石到毛泽东,都认同孙中山的“训政”论。在民国初年,孙中山说是反袁世凯战争失败,是由于革命党人都不听他的话,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人民的程度太低,必须在武装夺权后实行“训政”,用他的孙文学说狠狠教训百姓若干年,然后赏给他们一部宪法,实行“宪政”。蒋介石上台便照计而行,效应就是“训政”数年,训出了日本侵占半个中国,也训出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及其后的红色政权。等到蒋介石被毛泽东打败,想到以“宪政”救命,但被钦定国民大会选成总统不过年余,便滚到台湾再度“训政”去了。
毛泽东反蒋曾受众多民主人士的拥护,只是不久便对这班人士和知识分子好对他的决策说三道四,感到不耐烦,由肃反、思想改造到批二胡(胡适、胡风),再以百家争鸣“钓鱼”,接着就是那场把55万高中级知识分子打成阶级敌人的“反右斗争”。由“文革”史表明,毛泽东至死仍在坚持“训政”。他去世后,情形有改变,众多已故或在世的大师,被平反昭雪。
据我的了解,虽有个别学者以“应帝王”为己任,但大半都认同人类社会应有普世价值。因此他们无不是坚定的爱国者,中华文化的捍卫者,而罕有人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都在各自的领域,为促使中国超越现状而走向世界前列,尽心尽力。
三、大师的实例
例如马相伯、蔡元培和陈寅恪三位。他们的信仰和追求,理念和学说,自我定位和社会评价,都有很大差异,却都是盖棺可以论定的大师。
马相伯即马良马建常,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在信仰上与满清到民国历届政府不断强调的尊孔读经,格格不入。但他是现代教育的实践家,震旦、复旦、辅仁三所名校的创办者。他在清末就提倡的“读书不忘爱国,爱国不忘读书”,不仅为张之洞激赏,还在民初成为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的理念。他在教会内部反对梵蒂冈任命的洋主教剥夺华人自主传教的谬论,但在民初又坚持反对康有为、陈焕章要以孔教为国教的言行。正是他坚持信仰自由、教育自主以及对于袁世凯、蒋介石的文化专制都挺身批判,才使他得到举国敬重的百岁哀荣。
蔡元培以清末进士并点翰林,却成为民间办学的楷模,同盟会前身之一光复会的创始人。辛亥革命伊始,他就成为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立下的不朽业绩,便是废止全国学校的尊孔读经。后来他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恪守“兼容并包”的学术自由理念,将官僚养成所的北京大学,转型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以后他宦海浮沉,也曾列名国民党右派的“清共”提案。但他随即赞成宋庆龄发起的保卫民主大同盟,并在国民政府体制内,创办大学院、中央研究院,力求给教科文诸领域的学者,开拓自由研究而激励创新的生态园地,证明他确实无愧于教育现代化的大师称号。
陈寅恪则以纯学者而名垂青史。他于清末民初在日本欧美长期留学。他不在乎学位,却在乎追求新知,因而成为在瑞士听过列宁演讲的第一个中国人。他对古今语言文字掌握多达十七八种,他对中西社会历史的认知,在同辈中几乎无人能及,以致他没有学位没有论著,被新成立的清华研究院聘为导师,而经他指导或听讲的研究生,以后多半成为名闻遐迩的大学者,并终身以曾名列陈氏门墙为荣。陈寅恪的历史论著不算多,但大都成为文史研究新门类的开山名作。然而作为文史大师,他留下的最大遗训,莫过于作为学者,必须具有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说到做到。曾拒绝蒋介石的拉拢,不像冯友兰、顾颉刚那样热衷于跻身“国师公”。也曾拒绝出任中国科学院历史二所所长,明知那是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指名,却坚持如果就任,所内研究不可跟着意识形态转悠。他在解放初拒赴海外,甚至拒赴香港,证明他是真诚的爱国主义者。但他恪守学者的人格独立和思想自由,也使他付出了巨大代价。这位国宝级大师,竟没逃脱左祸,“文革”开始,年已八旬,仍被红卫兵恶斗致死。
四、真大师的群体意义
大师中的悲剧人物,常常体现坚持真理或者恪守真知,反而被指斥为悖时逆说乃至心怀叵测。郭沫若对王国维、胡适、陈寅恪等的政治批判,便是显例。
于是,略说在新世纪的开端,向观众更其是青少年学生介绍教科文卫诸领域大师的必要,似乎不算辞费。
那必要,在我看来至少有这样五点。
第一,中国人决不缺乏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非但在科学技术领域,众多大师堪称本专业的第一流专家,其成就往往前无古人,也置身于世界前列。即如深受权力疑忌干扰的人文社会学科,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当做治学准则的,也所在多有,代不乏人。除王国维、陈寅恪外,费孝通的社会人类学、周予同的中国经学史、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理学等,都是前现代没有的或仅见雏形的新学科。
问题是中国的社会政治环境,虽然今昔不同,却未必有利于自然科学、人文社会学科的创新。毛泽东提倡“革命的实用主义”,晚年更要对自然科学家划阶级,因而理论的自然科学难以昌明,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诸学科只能变成当前政策的注脚,而文史哲研究更时时要提防棍棒。这样的威胁没有消失,而“见利忘义”又已弥漫教科文卫的每个行业。人们追根溯源,归因于中世纪式的权力机制,并未跟着“文革”而被彻底否定。百年来大师多悲剧人物,岂非明证。
第二,我们民族的文明进程,以大师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是主要的动力。无论主流舆论如何否定,什么“知识分子最无知识”、“高贵者最愚蠢”、“书读得越多越蠢”之类,都不能改变百余年来,中国的每一变动,促进者都是学者文士。即使反变革方面,欺世盗名或助纣为虐的主角,也必是知识分子。上世纪中叶在中国愈演愈烈的反智主义运动,恰好反证知识分子对于公开的变相的专制主义,都是难以克服的障碍。
第三,中国要走向现代化,如王元化所说,需要有学问的思想家,有思想的学问家。这正是教科文卫各领域内大师的写照。古称觉悟未知的事理曰学,有所不知待人解答曰问。因而大师作为学问家,必定好学不倦,不会不懂装懂,但他们做学问,必定用自己的头脑思维,不会人云亦云,从而形成自己的认知体系。在这一点上,真大师体现的共性,令人印象深刻。
第四,为青年学人树立榜样。上世纪中叶以来,学风文风陋劣,教育领域弊病尤甚。无论大中小学,总视有学问有思想的教师为异己,当做改造乃至革命的对象。相反,曲学阿世或者不学有术之徒,常可名利双收,成为学界的不倒翁。这在年轻学生看来,与时俯仰最保险,坚持真知很可怕,追逐权力才有利,那效应就是置公共利益于不顾。各行各业的杰特人士的成长过程,让青年学人开始了解怎样做一个真正的有出息的人。
第五,向现行的学术文化政策提出了问题。比如说对知识分子以左中右划线,把“听话”、“紧跟”、会揣摩、善附会等,当做人文社会学科是否为己服务的尺度,赏以高位,歆以重利,以致欺世盗名的假大师层出不穷。我们的教科文卫当局,普遍面临诚信的缺失,而表彰假大师,阻遏人们对学术骗子、文化流氓的揭露批评,无疑是一大原因。但愿官位与智商背逆的某些教育文化决策者,能悟出一点什么。
我相信中国可能有活着的大师,惜因寡闻而未见。我也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随着文化生存环境不断改善,未来必定大师越来越多。不过由生者来看,只见假大师得意,未见真大师发声,不禁想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再版跋所揭示的,“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是否意味着我们的学术评价机制,尚不足以判别真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