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中义:大学生何以“精神成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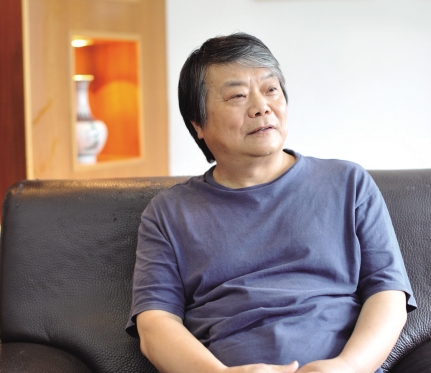
夏中义:教授、博士生导师
大学生何以“精神成人”?
几乎每一个大学生都相信自己已经“成人”。
他们通常是在生理学与法学层面来理解“成人”:前者是指身体发育,长个儿;后者是指领取身份证,享有宪法规定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可以脱离父母的监护。但这不是价值层面的“精神成人”。
大学生“精神成人”,关键是看他(她)能否在本科四年间(通常为18至22岁,即其生命史上一段特殊的“灵魂发育”季节)持续且认真地问自己如下问题:怎样做人?做怎样的人?怎样才能有一个现代公民所须具备的独立精神和思想……谁也无权强迫或苛求所有大学生都应思考上述命题,但我们的社会及大学无疑有责任创造一种氛围,能有效地引导大学生对自己的生命或日常生存有价值关怀,而不是被时尚牵着鼻子走,更不应对粗鄙化的种种流俗失却精神免疫力。
重视大学生“精神成人”是利国利民的功德大业,那么,谁来管?
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当它刚从中世纪欧洲崛起时,本是以“精神城堡”的姿态,而不是以“职业培训所”的招牌昭示于世的。于是,人们有理由期待当今中国社会也作如是观。但在实际上,当今社会怎么看大学,可从每年高考前的填报志愿见出。高中毕业生怎么填报第一志愿是一个象征。社会流行什么,往往作为某种观念,无形但又深深地渗入学生及其家长的脑海,成为他们填报志愿时的重要参照。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高校有些专业非常吃香,比如金融、外贸、会计、外语、法律、行政管理等。这些专业为何能受到公众的青睐?这与中国社会近十年来的重大变化有关,经济体制发生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经济体制转型是影响中国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经济对于老百姓来说,首先意味着收入的多少,能否脱贫致富。而孩子上大学,毕业后找一个不错的岗位,有不错的收入,这几乎成了无数民众对大学的民间想象。这自有其价值的正当性乃至历史的合理性,因为底层平民对他们曾经经历或仍在忍受的困苦刻骨铭心,他们穷怕了。也因此,这种风气和观念不免诱导公众把大学仅仅理解成一种培训职业技能的场所。如此一来,大学极为重要的功能,即大学应是弘扬人文精神的旗帜,大学更应是大学生“精神成人”的摇篮,却不慎被忘却。当下社会演化所诱发的消费主义与实利主义倾向给大学生“精神成人”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容小觑。
应该说,大学生“精神成人”本是高等教育的天职,西方近、现代教育思想大师如纽曼、赫钦斯等更主张将此置于大学工作之首位。但遗憾的是,当今中国大学在教育大学生“精神成人”方面的缺失是长时段,结构性的。中国高校及其职能部门也做学生工作,重在政治导向与心理调节,这与笔者所企盼的,高校应为大学生“精神成人”提供课程化的、旨在传承人类共同体的普世价值谱系的优质思想资源,差别甚大。
大学生“精神成人”其实质是“价值论”命题,而非“知识学”命题。所以,若将大学生“精神成人”理解为课程设置层面的“文理互渗”,即让文科生读点“理”,理科生读点“文”,未免舍本逐末。
同时,我也不认为文科生由于专业是读文史哲就一定有自觉的人文关怀。高校人文课程设置首先是着眼于专业角度的;至于能否将该专业课程可能含有的人文关怀讲清楚,讲透彻,亦即能否把人文关怀与专业教学相结合,这将取决于主讲教师的专业造诣、精神高度乃至人格力度。曾听到不少人批评高校文科有如下弊病:“学哲学的很空,学历史的很死,学文学的很浅。”话虽偏激,但不乏深刻。叔本华当年说过,德国大学里哲学教授很多,哲学家很少。我理解叔本华的本意大概是说,只有用自己的生命体验来奠基的哲学才可能是有活力乃至有原创性的真哲学,只有通过呕心沥血才领悟且构建哲学的哲贤才不愧为哲学家;而更多的哲学教授仅仅照本宣科而已。这样的教授也许能把课程讲得滚瓜烂熟,但他们酷似留声机,并没把灵魂放进去。学生可从其课程听到哲学史上某家写了什么书,有什么观点,但这个哲学家、这些哲学观点却与主讲老师的精神状态无关。假如从嘴里讲出来的哲学仅仅是一串飘忽在逻辑层面的词语,这些词语与主讲老师并没发生精神上的深刻关联,可以说,这样的哲学是贫血的,这样的哲学能不空吗?哲学是这样,历史是这样,文学也是这样。不论哲学教授、历史教授还是文学教授,倘若他们上课时能将专业知识与生命体验连在一起,与他们独立思考的大脑连在一起,那么,这样的哲学就不空,这样的历史就不死,这样的文学就不浅。在当下中国,文科教学理应担当起参与大学生“精神成人”的责任。但若仅仅从知识角度来讲人文学科,意义似乎不会太大。
高校文科在大学生“精神成人”领域尚且跛脚,理科不提也罢。谁来管大学生“精神成人”,看来是个问题。
文字来源:《解放日报》2003年07月0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