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力斌:杜甫再世 如何写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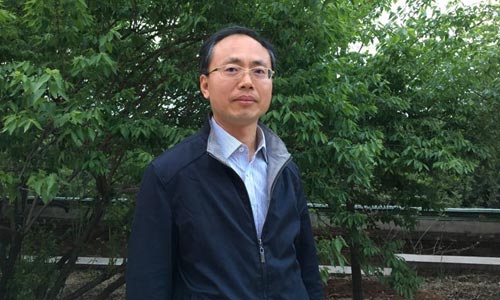
师力斌:《北京文学》副主编、诗人、评论家
摘要:在直面时代、捕捉时代的时候,杜甫始终保持其“正大”,这是杜甫的可贵,也是今天诗歌创作值得汲取的经验。
流动的历史、变动的现实无时不在提醒我们,拿出这一时代的文学创造来!捕捉时代,书写时代,而且将这种书写提升到正大之境界,这是杜甫的可贵,也是今天诗歌创作值得汲取的经验。
诗歌的时代性是一个问题。所谓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除了有对唐诗、宋词、元杂剧、明清小说等文学外在形式更替的关注,更重要的是对文学内在规定性的理解,那就是,新一时代的文学,不但不能是对旧一时代文学形式的“抄袭”,而且也不能是思想内容上的抄袭。文学的历史惯性必须适应新鲜生动的现实,文学内在的稳定性必须适应文学外部的变化,也就是文学要积极适应时代。
在认识和表达时代性上,当代新诗有不少成功之作,但是一些无视时代、回避时代的诗歌写作也需要警惕。现如今,找一首赞美乡野的诗容易,找一首深入刻画城市品格的诗歌则难。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古典意义上的田园时代已经远去,但仍以茂林修竹、古道西风、枯藤老树的形式,顽固地停留在诗歌书写中。出现在编辑案头、印刷在雪白纸面上的,依然不乏超历史、超现实的田园想象、隐士趣味、牧歌腔调,依然是陶渊明的采菊东篱,王维的空山新雨,戴望舒的丁香女子,海子的太阳、麦地、大海、姐妹。这些诗作或许有它们文学上的存在空间,但若一概如此、一味如此,新诗创作将误入歧途。诗歌退入历史、退入自然、退入身体的风气曾一度流行,浅薄地附庸风雅、热衷炫耀小资情调、一味迷恋身体书写的诗作并不鲜见。由于无法或无力呈现时代感,便争相躲到敷着现代性面膜的复古主义或形式主义之后,这种诗歌妆容与我们的时代还有何联系?
诗歌脱节于时代这一病症,倒让我一次次怀念起杜甫来。如果出这么一个选题:以回家探亲为主要情节,写一个关于战争与和平、个人与国家为主题的作品,其中要有时代背景、历史事件、人物形象、山川地貌、风物景观、战场场面、难民状况、妻离子散、儿女情长、家国情怀、人道主义等诸多元素,不超过七百字。能不能写出这样的作品?这个看上去似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却被杜甫完成了。作为其诗歌艺术集大成之作的《北征》,正是这样一个经典作品。杜甫之所以为“诗史”“诗圣”,就在于他从来都是直面时代,捕捉时代,主动吸纳,吞吐自如,对于时代,他的诗作有着非凡的容纳力和卓越的表现力。如果杜甫活着,阿里巴巴、小米科技这些时代新声可能早就入诗了。
更重要的是,在直面时代、捕捉时代的时候,杜甫始终保持其“正大”。叶嘉莹说杜甫胜在“博大、均衡与正常”,博大指他在诗歌体式上的“汲取之博”,均衡与正常则指杜甫有一种“健全之才性”,不仅在诗歌的体式、内容与风格方面集大成,在修养与人格方面也有大境界。如论者萧涤非所言,杜甫的感情“不但是真实的,而且是重大的”,有分量,有巨大内容,和人民的感情息息相通。博大、均衡、正常、健全、重大感情,我将这几个方面统称为“正大”。“正”是就其方向而言,与偏激、怪诞、离奇、费解之情感倾向相区别,不会刻意追求一种与众不同的怪诞离奇,怪力乱神;“大”是就其含量而言,举凡民族兴亡、战争和平、边关安危、民众离乱、人生成败、官场得失、骨肉亲情、日常生活,这些从大到小的事宜,一概囊括诗中。诗可以微小、细小,但不能狭小、渺小;诗可以重大、宏大,但不能空大、疏大。杜甫写鹰,写马,写鱼,写桃,写古柏,写新松,都将他自己的感情带入。同时,无论多小,他的视野中总有宇宙,有家国,有黎民百姓,这些思想感情根深蒂固地长在他的心中,造就了他诗歌的正大之气。
面对今日一些诗歌的“化妆术”,杜甫的正大恰是一面明亮的镜子。它证明了时代书写和个人抒怀并不矛盾,载道与言志并不抵触。“致君尧舜上”“虽乏谏诤姿,恐君有遗失”,杜甫的诗自然属于载道,但无论是关注现实时事,还是同情贫弱底层,都非故意为之或随意拔高,而是他的思想感情自然而然的一部分。他表明,优秀的载道是一种政治情怀,不仅不会干扰言志,而且会丰富、拓展言志的视野。从实践的角度来看,载道的难度要远远大于言志的难度,因为它要求思想更丰富,视野更开阔,思考和关心的问题更复杂,面对和处理的经验也更深广。毕竟,处理一个时代的复杂心理远比处理一己之感受要困难得多。
田园牧歌的古典趣味固然让我们留恋和回望,但流动的历史、变动的现实无时不在提醒着我们的新诗:拿出这一时代的文学创造来!捕捉时代,书写时代,而且将这种书写提升到正大之境界,这是杜甫的可贵,也是今天诗歌创作值得汲取的经验。
文章来源:《人民日报》,2018年5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