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庆炳:谈谈文学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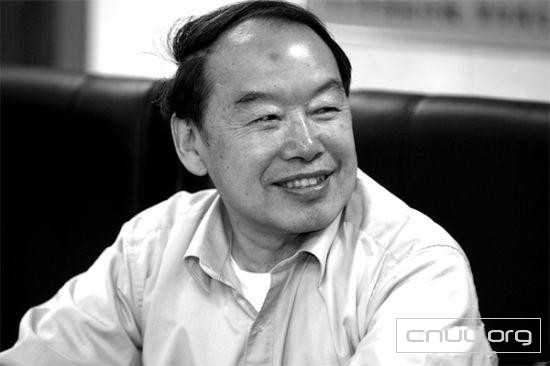
在文学理论中,不是所有的概念都是有意义的。有的概念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文学的变化而逐渐失去了意义,如20世纪50~60年代我们喊得最响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中国新时期以来文学的变化,已经失去了现实意义。但有一些概念却历久弥新,下面我们要谈论的文学性就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常论常新的概念。我曾读过一篇题为“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的漫延”的论文,意思是在电子媒介时代文学作品已经没有多少人阅读了,但文学性却仍然在各类文化产品中存在。且不说这篇论文的观点如何,仅就其题目看,文学性是一只不死鸟,文学终结或将要终结,文学性依然要漫延下去。还有,近几年中国制造的一些电影大片,虽然吸引了部分观众,但遭到一些专家的批评,说这些大片缺乏文学性,很糟糕云云。可见文学性是一个重要的概念。那么什么是文学性呢?我们应如何理解文学性呢?
一、文学性术语的提出
文学性是上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学派提出来的。俄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形式主义批评家罗曼·雅各布森(1891-1982)在上世纪20年代提出了文学性这个术语,它指的是文学的特性。他说:“文学科学的对象并非文学而是‘文学性’,也就是说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雅各布森对当时各种社会学的、心理学的、政治学的、哲学的文学研究表示不满,认为这些研究者就像一个警察,把凡是来过这个房间里的人,甚至是经过街边的人都捉起来,而不看他是不是“文学”本身。他的意思是,要把文学与非文学区分开来,要揭示文学的特性,然后再把文学的特性即文学性作为文学科学的研究对象。那么文学性在哪里?对于雅各布森和其他俄国形式主义者来说,文学性只存在于文学的语言层面里。因此,他们热心于“诗的语言”与“实际语言”的区别或“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的区别。雅各布森提出,文学性就在作家对日常语言加以变形、强化甚至扭曲中,“对普通语言实施有系统的破坏”。
举个例子来说:“你知道小兰昨天已经离开北京了吗?”“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我们也能凭着直觉,知道前面一句话不过是传达了一个信息的日常语言,而后一句就是有明显节奏的、有韵调的诗句,即便我们不知道后一句出自杜甫的名篇《赠卫八处士》。文学性就在这不同寻常的诗句中。在俄国形式主义学派中,对于文学性最著名的解释,来自什克洛夫斯基的《艺术作为手法》一文。在这篇论文中作者提出了文学语言陌生化原则,他认为,陌生化是和自动化相对的。自动化就是我们感觉自动化。例如你第一次开汽车上马路的情境,尽管已经过去多年,可你还是记得自己第一次开汽车上大街时那种战战兢兢的、唯恐发生意外的心情;但现在你已经开了多年的车,十分熟练,甚至可以一边开车,一边打手机。前面那种让你永远不会忘记的情境属于陌生化,后面的情境则属于自动化了。陌生化让我们的感觉敏锐起来,这正是文学所需要的。所谓文学语言的陌生化就像前面我们所举的杜甫的诗句“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这里用两个星宿为喻,说明人生不相见,动辄就像参与商那样,永远不会同时出现在同一个天空。这就变成与普通的日常生活语言不同的文学语言,这就是文学性。的确,诗歌中有很多特别让人感到陌生的句子:“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李白);“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欧阳修);“我的寂寞是一条蛇,静静地没有言语”(冯至);“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数百年来纺着疲惫的歌”(舒婷)……这些特别的诗句的确让我们感受到文学文本的文学性。
二、文学审美特征论对文学性的理解
但是我们能不能仅仅从语言的层面去理解文学性呢?这是不能的。文学是发展的,文学观念也是发展的,文学性也因此是变化发展的。有多少种文学观念,就会有多少种对文学性的理解。中国古人讲“诗言志”,与“言志”相关的“赋、比、兴”就是中国古人心目中的文学性。曹丕说“文以气为主”,气韵就是曹丕心目中的文学性。刘勰说“情者文之经”,情性就是刘勰心目中的文学性。韩愈讲“文以载道”,道统就是韩愈心目中的文学性……亚里士多德把文学的特性理解为“摹仿”,摹仿性就是亚里士多德视野中的文学性。华兹华斯把诗歌理解为“强烈感情的自我流露”,感情性就是华兹华斯视野中的文学性。黑格尔认为文学是理念的感性显现,感性就是黑格尔视野中的文学性。别林斯基认为文学特性是用“形象”复制生活,形象性就是别林斯基视野中的文学性……文学性总是随着文学观念的改变而改变,这也正是文学性的复杂性所在。
那么,我们今天应如何理解文学性呢?随着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开始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运动,我们批判了“文革”时期的文艺极端政治化和工具化的做法,并冲破了“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思想束缚,也从长期以来就规定的文学的特性是“形象”的单一理解中解放出来,特别是80年代初掀起的“美学热”的滚滚浪潮,使大家在讨论中逐渐形成了文学的特性是审美的共识。这就是说,审美是区别文学与非文学的根本特征。那么什么是审美呢?审美,最简明的概括,就是情感的评价。人都有情感,人的感觉、知觉、感情、回忆、联想、想象、理解等都是人的情感要素,人以自己的情感去评价周围的生活,就会产生美、丑、悲、喜、崇高、卑下等各种情感体验,这就是审美所获得的体验。看到春天的花开了,感到新鲜美丽,觉得欣喜,情不自禁要拥抱大自然;看见贪官贪污受贿,感到丑恶,引起愤怒,必欲除之而后快;阅读一部文学作品,读到某个人民英雄为国家为民族英勇牺牲,感到他的崇高,也为英雄的死感到悲壮;听了一段相声,里面的小人物的对话,让你联想起生活中的情境,你突然笑了起来。这一切都可以叫做审美。文学是作家以自己的情感去评价生活,作品里面所描写的生活都经过了作家的情感过滤、渗透和评价,这才能让读者觉得那生活不是冰冷的,是带有诗人、作家的情感体温的。
请看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公元762年冬,唐军在洛阳附近打了一个大胜仗,收复了洛阳等地。763年正月,史朝义兵败自杀,延续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至此平息。消息传到当时杜甫的栖身之地梓州,杜甫闻信喜极而泣,写下了他的“生平第一快诗”。这首诗所写的是杜甫对于平定安史之乱消息的反应,也是写他对这一事件的评价。杜甫是以自己的手舞足蹈的兴高采烈的情感来评价这个事件。换言之,杜甫的诗,不是客观报告这个消息,不是消极地复制这个消息,而是带着自己的十分高兴的情感来评价这个消息。这种评价是全面的:以至于喜极而泣,以至于手足无措,以至于放歌纵酒,以至于幻想立刻回家,连回家的路线也在瞬间想好了……由此看来,今天我们既然把文学的特性理解为审美,那么审美性就是我们所理解的文学性。
三、文学性在具体作品中的表现
进一步的问题是,作为文学性的审美性在具体的文学作品中是如何表现出来的?作家在以情感去评价周围事物的时候,获得了自己的审美体验。如果作家把这种审美体验转化为语言文本,文学性也就产生了。那么文学性体现在语言文本的哪些方面呢?我认为,“气息”“氛围”“情调”“韵律”和“色泽”就是文学性在作品中的具体的有力的表现。
气息是指语言文本中所呈现的人的鲜活的生命力。审美的主体是人,审美评价的主体也是人。具体到语言文本中,文学性的第一因素就是人的气息。古人说,有气则生,无气则死。人是如此,作品也是如此。作品中有气息,有鲜活的生命力是审美的首要条件,同时也是文学性的首要条件。中国古代文论所主张的“气韵生动”,曹丕的“文以气为主”,所讲的都是作品的气息,即作品中生命力的表现。尼采说“在所有的作品中我最喜欢的是用鲜血写成的”。美国现代美学家苏珊·朗格在《艺术问题》十讲中,专门用一讲的篇幅来谈论艺术的生命问题,她认为艺术品并不会呼吸、睡眠、吃饭、自我恢复、生育繁殖,它不是生命本身,但它必须是生命的形式,有活力,栩栩如生,生命的一切特征——有机性、动态性、节奏性与不可侵犯性——都必须在作品中成为生命的投影。尼采与朗格,一古一今,所讲的也是文学艺术的生命气息。的确,死的作品是不会成功的,唯有呼吸着生命气息的活的作品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品。上面所举《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其优点之一,就是洋溢着生命的气息,我们透过那些鲜活的诗句,看到了诗人杜甫听到好消息后那种欣喜欲狂地跳跃与呼喊的样子,特别是“涕泪满衣裳”“漫卷诗书”“白日放歌”“青春作伴”等语句,真是用喜极而泣的泪水写出来的,是用长久艰难等待胜利的心血写出来的。每一个句子都像一个兴高采烈的人的手舞足蹈。
氛围指语言文本中人与人、人与事、人与景的关系所流露出来的情感性气氛。文学作品总是在写人与人、人与事、人与景的相互关系中推进,如果作家真正用情感的眼睛去看待生活、描写生活、评价生活,那么就一定会使人与人、人与事、人与景的关系透露出一种气氛来。一个刚刚经过严冬的荒寒孤寂的人,来到了春天的原野,眼前是一片草木的新绿,在直觉的瞬间,他会把人与严冬的景色、人与早春的景色的关系不自觉地进行对比,从而感到那春天的新绿向他拥抱过来,他感到一种欣喜的气氛在他周围弥漫开来。这是我们在生活中感受的氛围。在文学作品中,诗人、作家如果也是用这种情感的态度去描写这些关系的话,那么情感性的气氛——氛围,也会在作品中呈现出来。如王昌龄的《从军行》(其二):“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这首诗所写的无疑是“边愁”,但这战士的“边愁”与“琵琶”“舞”“秋月”“长城”是什么关系呢?为何让我们觉得加了似可有似可无的“高高秋月照长城”这一句,那战士的“边愁”就无比凄凉、无比深厚呢?为何这首诗让我们感到一种无限感伤、悲凉的气氛呢?原来在这里诗人的审美情感让“边愁”与“琵琶”“舞”“秋月”“长城”形成了一种互动关系。“琵琶起舞换新声”作为一种反衬,不但不能让战士高兴起来,反而让战士的“边愁”在歌舞的衬托下更显悲凉。“高高秋月照长城”则让山河大地都化为“边愁”,而“边愁”也化为整个山河大地,即把主观的“边愁”与客观秋月下的“长城”交会在一起,使“边愁”显得更为无限无垠、无边无际,一种荒凉萧瑟的气氛在我们心中弥漫开来。
情调指语言文本中所呈现的感情的各种格调,如乐观的格调、哀愁的格调、明朗的格调、忧郁的格调等。在文学创作的审美活动中,情感对于作品主题的塑造是造成情调的主要原因。作家写的可能是一个普通的事件,但却是用自己的特定的不平凡的情感灌注的,那么这被描写的普通事件也可以表现出不平凡的主题,从而呈现出特别的情调来。作家也可以写一个奇特的事件,但他可以赋予作品主题以平凡的情感,从而改变原来素材的情调。王蒙在上世纪80年代写的短篇小说《风筝飘带》,不过是写一对北京知识青年因谈恋爱不易找到地方的普通故事,但作家把一种雨过天晴般的带有希望的情感渗透在描写之中,使这篇小说的主旨具有一种明丽向上的情调。小说从范素素在傍晚时分等候男朋友佳原开篇,写他们这一个晚上频频寻找一个能够坐下来谈恋爱的地方,然而如此宽阔的北京,竟然找不到一个这样的地方。如果谁知道这个大概的故事情节,觉得这篇小说琐屑而又乏味,不值得一看,那么他就错了。原来作家用了一种超脱的、幽默的、风趣的笔墨来写这些人物与场景,强调的不是他们对环境的不满,而是“文革”已经结束,社会变革已经开始:“红底白字的‘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挨得很紧的惊叹号旁边,矗立着两层楼那么高的西餐汤匙与刀叉,三角牌餐具和她的邻居星海牌钢琴、长城牌旅行箱、雪莲牌羊毛衫、金鱼牌铅笔……一道,接受那各自彬彬有礼地俯身吻向她们的忠顺的灯光,露出了光泽的、物质的微笑。”然后写白杨树,女主人公范素素打扮得花枝招展站在这广告牌与白杨树之间等候她的恋人佳原。这个拉得很长的句子,是为了表示改革开放已经开始,中国已经走出了“文革”的泥淖,他们不必留在草原和农村,回到了北京,并且可以开始谈恋爱了,尽管范素素只是一个小饭铺的服务员,佳原则连工作都没有找到,在街道服务站给人家修理雨伞,尽管吃饭还要用粮票,尽管没有结婚的房子,尽管一切条件都还很差。作者强调的是佳原很忙。忙什么?忙着修雨伞的同时,开始看书,看优选法的书,看古生物学的书。作家强调在佳原的影响下,范素素也很忙,除了忙着端盘子,也开始学习阿拉伯语……作者强调佳原总是随遇而安,一段栏杆,一棵梧桐,一道河边,就满足了,可以和范素素依偎在一起,用阿拉伯语、英语交谈,尽管交谈起来结结巴巴。作者强调他们是幸福的,虽然暂时一切都还很难——找称心的工作很难,结婚也很难,因为没有分配到房子。但风筝已经放起来了,尽管他们还是风筝屁股后面的飘带,但新的时代、新的生活迎面扑来,保不准他们的梦想有一天会实现。作家暗示读者,说不定哪一天佳原会成为中国新一代著名考古学家的代表,而范素素呢,她的阿拉伯语经过大学的锤炼已经炉火纯青,她可能到外交部,说不准有一天要到某个阿拉伯国家的大使馆赴任……这虽然是一个秋天,但离春天已经不远了。小说的主题就是“风筝飘带”,写一个乍暖还寒的季节,我们似乎从这里闻到了春的气息。作家用自己的喜悦的感情改造了他笔下的材料和故事,整个文本透露出明丽和乐观的情调。
韵律指语言文本中的节奏、声韵的和谐程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的节奏和声韵是文学的音乐美的主要表现。诗是有音律的纯文学。诗比散文更讲究情趣。情趣的表现往往要求往复循环、缠绵不尽。这就要求有音律的配合。例如《诗经》中的四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朱光潜先生所说,如果译成散文,则为:“从前我走的时候,杨柳还在春风中摇曳;现在我回来,天已经在下雪。”朱先生的分析是:“原诗的意义虽大致还在,它的情致就不知去向。义存而情不存,就因为译文没有保留住原文的音节。实质与形式本来平衡一贯,译文不同原诗,不仅在形式,实质亦不一致。比如‘在春风中摇曳’译‘依依’很勉强,费词虽较多而含蓄却反较少。‘摇曳’只是呆板的物理,‘依依’却含有浓厚的人情。”朱光潜先生在这里指出了诗是情感的流露,它的音律是伴随着情感的,翻译成这样的散行文字因失去了音律也就失去了情感。但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并没有说散文、小说不要节奏、不要音律,只要有审美性存在,就有情感存在,也就需要节奏、声律存在。在那些优秀的散文和小说中,由于情感的表现十分深厚,有的甚至接近于诗歌,因此也常常有鲜明的节奏和声律。节奏是自然现象的原则,高低、徐疾、长短、阴阳、向背,艺术是自然的感应,因此,说节奏是一切艺术的灵魂也不为过。还有声律,就汉语说,最为重要的就是平仄交替运用所形成的韵调。在一切语言文学作品中,无论是节奏还是声律,总是伴随着作家的情感态度的流露而呈现出来。朱熹说:“韩退之、苏明允作文,敝一生之精力,皆从古人声响处学。”而声响之所以重要,就是与前面讲的气息相关,所以韩退之说:“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古人推重声韵的话还很多,引用不尽。即使在散文、小说中,凡是特别优秀的作品或多或少或强或弱,都有节奏、声律在运动,从而构成韵律的美。声律节奏在一般科学论文中不必强求,但在文学作品中则因为表现感情的需要,而不能不十分讲究。虽然不能做到像诗歌那样严整,但却要做到“无一定之律,有一定之妙”。《史记》《红楼梦》的某些片段,都朗朗上口,节奏自然,声律优美,是文学性的有力表现。
色泽指语言文本中所呈现的色彩的美。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不能像绘画那样着色,不能像要求绘画那样要求色彩丰富,但是在一些优秀的作品中,诗人、作家仍然讲究色彩的明暗和冷暖。前面提到的杜甫《赠卫八处士》,中间写到处士招待杜甫,有“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的句子,色彩十分丰富,春天的韭菜是绿色的,米饭则是白米与黄米相间的二米饭。我们可以想象,卫八处士招待老朋友杜甫,虽然没有什么山珍海味,但却尽其所有,素朴中不乏五光十色,加上家酿的美酒,也就十分丰富了,所以后面两句是“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两人喝酒喝得酩酊大醉。更重要的是全诗歌颂友谊地久天长,像“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等句,写欢迎杜甫的场面,是暖色调的,但“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则又是冷色调的。人生易老,昔日的朋友先后离去,多么让人感伤。这种冷色调和暖色调融合在一起,来源于朋友相见的感伤和愉快,是自然情感流露所致,也是审美性的呈现。
对于文学性来说,气息是情感的灵魂,情调是情感的基调美,氛围是情感的气氛美,韵律是情感的音乐美,色泽是情感的绘画美,这一个“灵魂”四种美几乎囊括了文学性的全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