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文:在我们的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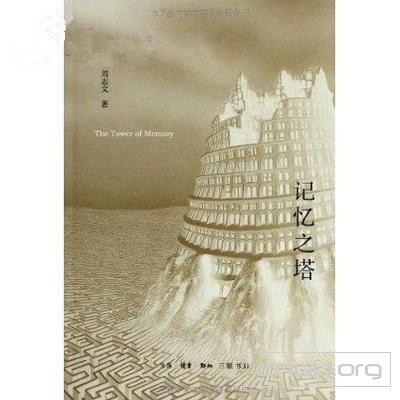
海明威早年有一本小说,书名是《在我们的时代》,这本书的主角名叫尼克,明眼人都知道就是海明威本人。书的第一篇名叫《印第安营》,写的是十岁大的尼克一次跟随他做医师的父亲与叔父到印第安营出诊的故事。一个印第安妇人难产,他父亲赶去急救及接生,妇人在床上辗转反侧大声号呼,痛苦异常,而妇人的丈夫因腿伤躺在上铺。尼克的父亲没带止痛药,带来的手术工具也很简陋,手术时必须尼克协助,因此他得以目睹所有的过程。最后他们总算顺利地帮她产下了一个男婴,当他们向睡在上铺的妇人丈夫道贺时,发现那男人已不堪折磨,竟在床上自杀了。
尼克在十岁的那年就经历了一场真实的出生与死亡,两种都是痛苦万分,都是受尽折磨的。他在回家的独木舟上问他父亲:“人死会很难吗?”他父亲说:“那要看状况而定。”其实尼克的问题还包括了人活下来也会很难吗?如果问了,他父亲可能会说:“那也要看状况而定。”
不只生死,其他的事,也得看状况而定,人的一生,好像并没有太多十拿九稳的事。我在高中之前,从来没想到自己会离开宜兰那个小地方,会到台北来“鬼混”了大半辈子,我后来在台大读了学位,最后还在那里任教,这些事完全出乎我当时的“预料”。一次初中的同学在台北聚会,一个同学说以前谁也想不到谁后来会是什么样子,我们班上一个家世好、成绩好的孩子,当时大家都以为他会最有成就的,想不到他后来继承了一间杂货店,门面越来越小,后来弄到关门了,自己也落魄的不得了。他又举我的例子说,我初中留级的时候,没有人想到我以后会当教授的,另一个同学开玩笑说,就是因为他留级多读了一年书,后来才有机会做教授呀,这话引起一阵笑。他们说的,笑话层面的居多,但其中也包含了部分的真实。
生命中的许多意义,是要在很久之后才发现的。就以我初中留级的事来说,我后来能够从事学问,并不是我比别人多读了一年的书,那一年,我不但没有多读什么书,反而自怨自艾得厉害,其中还包含了一段自毁的经历,四周没有援手,幸好我平安度过。然而那次“沉沦”,使我第一次感受到人生某些极为幽微但属于底蕴性的真实。譬如什么是假象什么是事实,哪些是背叛哪些是友谊,何者为屈辱何者为光荣……那些表面上对比强烈而事实是纠葛不清的事物,都因这一阵混乱而重新形成了秩序。那秩序并不是黑白分明的,更不是像红灯止步绿灯通行那么的当然,而是黑白红绿之间,多了许多中间色,有时中间色相混,又成了另一个更中间的中间色。真理不见得越辩越明,而是越辩越多层。以前再简单不过的,后来变得复杂了;以前再明白不过的,后来变得晦暗了。我与我的亲人、朋友、老师与同学,人挤人地住在同一个世界,但每个人都活在不同的层面里,彼此各行其是,关系并不密切。人必须短暂跳脱,才看得出你与别人以及你与世界的关系,这层关系也许不像一般人所说的那么是非判然、黑白分明。当我眼前不再是红绿的灯号的时候,那状况让我欲行又止、欲止又行,我觉得进退失据的困顿与荒谬,但齐克果说荒谬是真实的另一种称呼。
我在“受伤”之后,得到了这个思想上的宝筏秘籍,它告诉我要暂时跳开,我记得爱因斯坦说过:“一条鱼对它终生游于其中的水会知道什么呢?”暂时跳开帮助我看出事情的真相,而真相不见得只有一个。不只如此,我在以后的人生中,屡屡遭逢不同的挫折,每次挫折之后,都有另一种力量在心中兴起,这使我对挫折有了新的看法。
在我们的时代,信任与背离,荣耀与嘲讽同时存在。我不知道我是否真的该感谢我后来在东吴所受的“教育”。台大没有想象中的好,虽然台大的朋友都很优秀,但整体而言,却涣散得没什么精神,这也是台大一向的“传统”。我记得我读博士班的时候,被“分配”给裴普贤老师,做她麾下的一名“导生”。裴老师是台大中文系最早的教师之一,她说当她来台大做助教的时候,中文系第一届毕业生后来成为中文系名教授的叶庆炳先生还是学生呢。有一次她参加全球校友在台大旧体育馆举行的年会,会场高悬着“发扬台大精神”的标语,一位校友问:“什么是台大精神呢?”老师与校友都陷入沉默,一位校友突发奇想地说:“台大精神就是:台大没有精神!”引起一阵叫好和大笑。后来裴老师说:“我想了好几天,终于发现那位校友说得很对,台大的特色,就是没有任何精神。”
没有精神表示彻底的自由,所以没有精神也是精神。但暗地里其实不然,台大标榜的自由缺乏高贵的道德视野,所以不能算是自由,顶多只是各行其是的散漫罢了。有高贵道德视野的自由是把自由的境界放在别人甚至全体人类之上,所以不是自私的,真正的自由论者,并不放纵自己的自由,反而从外表看起来似乎还更加的拘谨与自制。
整体而言,我们置身的是个虚假与真相并存的世界,一个道德崩溃又有新的道德在试图重建的时代。失望的事很多,但也无须彻底绝望,总有一些事让你不经意发现,在那里也藏着不少的可能,包括希望。
我们不妨先从希望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我们处身的时代是一个科技进步、医学发达的时代,这两项史无前例的进展,使得全世界绝大多数的人受惠。不要说在远古洪荒的时代,就以一百多年到两百年之前的世界与今天比较,还是《孟子》上说的“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的时代,试想一个中等人口的家庭中的妇人一天忙在三餐及洗衣上的时间要多少?才知道在我们的时代妇人幸福的程度,农人、工人亦复如此。从医学发达的角度而言,近五十年的进步尤其神速,我记得我在读小学的时候,周围有人得盲肠炎就算得了绝症,送到医院没几个人出得来,现在切除盲肠早已是很小的手术了,另外有关呼吸、消化及血液的疾病都有很好的治疗进展,今天一百个成功进行了手术的心脏病患,送进三十年前的病房,九十个以上将无法痊愈,其他病症也一样。现代医学的进展,使人类达到有史以来最高的幸福。
最重要在提高人类的智慧,这是人类真正幸福的凭借。所谓智慧,是大多数的人会想到人类比较终极的问题,而不被眼前的纠葛事务所困。在提高智慧之前,人要增进知识,医学与科技是知识,能够运作的民主政治也是知识,科学的知识告诉我们处理生活所需与面对疾病的方法,民主政治的知识告诉我们人有很多相同的部分,因此可以谋求“共识”。
所以在我们的时代,我们的世界正处于比以前空前“合理”的状态,这合理的状态也许空前但不可能绝后,世界还有许多不幸,也有许多委屈不平未获得伸张,但与长久的历史比较,人类目前所处也是最幸福的时代。对一些不承认人类进步的人,你只要跟他们举例说,就在大约一百年之前,许多欧洲的贵族还深信奴隶或有色人种是下等人,他们受苦是理所当然,而在民权观念领先的美国,还有很多人相信非洲裔、亚裔、拉丁裔及妇女根本不配享有投票权。人们才知道近百年来进步的不只在科技,在灵魂上的开发也大有进展,这一点证明我们生活在现代的人类何其有幸。
有些知识的力量可以促成幸福,有些知识的力量会产生苦难,就像教育有正面负面之分。也许目前尚无法判断哪一种力量此后将更占优势,但两者我们都需了解,并试图去掌握它。这种工作不仅是知识上的,也是智慧上的。
在我们的文化认识中,中华文化占有相当重要的成分,我们必须重估我们的传统,因为这个传统自“五四”之后就被我们自己人轻贬得一文不值。问题是我们不能抛弃我们身上的所有,以便把自己变成外国人,当中国人是我们共同的命运,这是无法逃避的,必须共同面对,一味地毁弃自己的文化,跟自杀没有什么两样。
我们所处的时代,幸福与不幸都有,对知识分子而言,不幸的成分似乎更多一些。什么是一个真正的文化人?尤其在我们的时代。他必须认真地选择自己的价值,选定后就朝着这个方向走,所谓“虽千万人,吾往矣”。少说话,最好是默默无言。这是我为什么艳羡那些善于独处的人,他们在另一个世界找到了生命的中心,自信又从容地走自己的路。在我们的时代,世界有好的一面,也有很坏的一面,不能一概而论,很多事真如尼克父亲说的:“要看状况而定。”天气时阴时晴,乍暖还凉,路是有的,但很崎岖,目标也很遥远,还是值得走下去。“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让我们三复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