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遇春:文学与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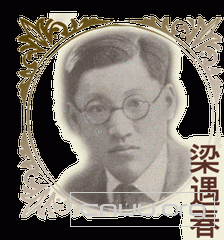
文学到底同人生关系怎么样?文学能够不能够丝毫毕露地写出人生来呢?大概有人会说浪漫派捕风捉影,在空中建起八宝台,痴人说梦,自然不能同实际人生发生关系。写实派脚踏实地,客观的观察来描写,自然是能够把生活画在纸上,但是天下实在没有比这个再错的话。文学无非是叙述人的精神经验(述得确实,不确实又是一个问题),色欲熏心固然是人性一部分,而向渺茫处飞翔的意志也是构成我们生活的一个重要成分。
梦虽然不是事实,然而总是我们做的梦,所以也是人生的重要部分。天下不少远望着星空,虽然走着的是泥泞道路的人,我们不能因为他满身尘土,就否认他是爱慕闪闪星光的人。我们只能说梦是与别的东西不同,而不能否认它的存在,写梦的人自然可以算是写人。好多追踪理想的人一生都在梦里过去,他们的生活是梦的,所以只有渺茫灿烂的文字才能表现出他们的生活。无论多么实事求是抓着现在的人晚上也会做梦的。我们一生中一半光阴是在做梦,而且还有白天也做梦的。浪漫派所写的人生最少也是人生的大部分,人们却偏说是无中生有,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但是我们虽然承认浪漫文学不是镜里自己生出来的影子,是反映外面东西,我们对它照得精确不精明,却大大怀疑。可是所谓写实派又何曾是一点不差地描摹人生,作者的个人情调杂在里面绝不会比浪漫作家少。法国大批评家Amiel说:“所谓更客观的作品不过是一个客观性比别人多些的心灵的表现,就是说他在事物面前能够比别人更容易忘记自己;但是他的作品始终是一个心灵的表现。”曼殊斐儿的丈夫Middleton Murry在他的《文体问题》(The Problem of Style)里说:“法国的写实主义者无论怎样拼命去压下他自己的性格,还是不得不表现出他的性格。只要你真是个艺术家,你绝不能做一个没有性格的文学艺术家。”真的,不只浪漫派作家,每人都有一个特别世界排在你眼前,写实主义者也是用他的艺术不知不觉间将人的一部分拿来放大着写。
文学这面镜子是凸凹靠不住的,而不能把人生丝毫不苟地反照在上面。许多厌倦人生的人们,居然可以在文学里找出一块避难所来安慰,也是因为文学里的人生同他们所害怕的人生不同的缘故。
文学同人生中间永久有一层不可穿破的隔膜。大作家往往因为对于人生太有兴趣,不大去念文学书,或者也就是因为他不怎么给文学迷住,或者不甚受文学影响,所以眼睛还是雪亮的,能够看清人生的庐山真面目。
作家的作品也无非因为一时情感顺笔写去,来表现出他当时的心境,写完也就算了,后来不再加什么雕琢功夫。甚至于有些是想发财,才去干文学的,莎士比亚就是个好例子。他在伦敦编剧发财了,回到故乡作富家翁,把什么戏剧早已丢在字纸篮中了。所以现在教授、学者们对于他剧本的文字要争得头破血流,也全因为他没有把自己作品看得是个宝贝,好好保存着。看一看他们身旁五花八门的生活,他们简直没有心去推敲字句,注意布局。文法的错误也有,前后矛盾的地方更多。他们是人生舞台上的健将,而不是文学的家奴。热情的奔腾,辛酸的眼泪充满了他们的字里行间。但是文学的技巧,修辞的把戏他们是不去用的,虽然有时因为情感的关系文字个别非常动人。总而言之,他们知道人生内容的复杂,文学表现人生能力的微小。所以整个人浸于人生之中,对文学的热心赶不上他们对人生那种欣欢的同情。只有那班不大同现实接触,住在乡下,过完全象牙塔生活的人,或者他们的心给一个另外的世界锁住,才会做文学的忠实信徒,把文学做一生的唯一目的,始终在这朦胧境里过活,他们的灵魂早已脱离这个世界到他们自己织成的幻境去了。被艺术迷惑了的人才会把文学看得这么重要,由这点也可以看出文学同人生是怎样地隔膜了。 以上只说文学不是人生的镜子,我们不容易由文学里看清人生。
再说些文学对人生的影响吧。法朗士说“书籍是西方的鸦片”。这话真不错,文学的麻醉能力的确不少,鸦片的影响是使人懒洋洋的,天天在幻想中糊涂地消磨去,什么事情也不想干。文学也是一样地叫人把心搁在虚无缥缈间,看着理想的境界,有的沉醉在里面,有的心中怀个希望想去实现,然而想象的事总是不可捉摸的,自然无从实现,打算把梦变做事实也无非是在梦后继续做些希望的梦吧!因此对于现实各种的需求减少了,一切做事能力也软弱下去了。憧憬地度过时光无时不在企求什么东西似的,无时不是任一去不复的光阴偷偷地过去。为的是他已经在书里尝过人所不应当尝的强度咸酸苦甜各种味道,他对于现实只觉乏味无聊,不值一顾。不管是为人生的文学也好,为艺术的文学也好,写实派,神秘派,象征派,唯美派……文学里的世界是比外面的世界有味得多。只要踏进一步,就免不了喜欢住在这趣味无穷的国土里,渐渐地忘记了书外还有一个宇宙。本来真干事的人不讲话,口说莲花的多半除嘴外没有别的能力。天下最常讲爱情者无过于文学家,但是古往今来为爱情而牺牲生命的文学家,几乎找不出来。理想同现实是两个隔绝的世界,谁也不能够同时候在这两个地方住。
还没有涉世过仅仅由文学里看些人生的人一同社会接触免不了有些悲观。好人坏人全没有书里写得那么有趣,到处是硬板板地单调无聊。然而当尝尽人海波涛后,或者又回到文学,去找人生最后的安慰。就是在心灰意懒时期,文学也可以给他一种鼓舞,提醒他天下不只是这么一个糟糕的世界,使他不会对人性生了彻底的藐视。法朗士说若使世界上一切实情,我们都知道清楚,谁也不愿意活着了。文学可以说是一层薄雾,人看起不会太失望了。不管作家书里所谓人生是不是真的,他们那种对人生的态度是值得赞美、模仿的。我们读文学是看他们的伟大精神。我们这样所得到的大作家伦理的见解,比仅为满足好奇心计那种理智方面的明白人生真相却胜万万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