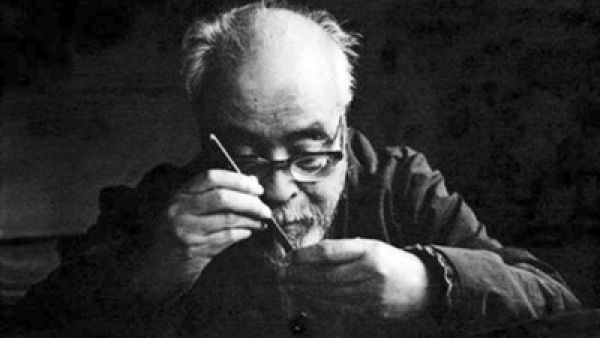冯友兰:北京大学

在十年动乱以前,北京大学校长陆平提出了一个办北京大学的方针:继承太学,学习苏联,参考英美。大动乱开始以后,他的这项方针受到批判,成为他的罪状之一。当时我也说过,北京大学的校史应该从汉朝的太学算起。不过,当时的批判并没有涉及我。
我所以认为北京大学校史应该从汉朝的太学算起,因为我看见,西方的有名的大学都有几百年的历史,而北京大学只有几十年的历史,这和中国的文明古国似乎很不相称。
现在讲北京大学历史一般是从清朝末年的京师大学堂算起,它是戊戌变法的产物。清朝的慈禧太后篡夺了政权以后,把光绪皇帝在变法的时候所行的新政都作废了,只有京师大学堂继续存在下来。这也可以说是戊戌变法留下来的纪念品吧。我跟着父亲在崇阳的时候,在他的签押房里看见过当时颁布的京师大学堂章程。用木板红字印的,有好几大本。当时我什么也不懂,只记得在分科之中有一科叫做经科。每一种经都有一个学门,例如“尚书门”、“毛诗门”等。在本科之外,还没有通儒院,大概相当于西方大学的研究院吧。
清朝的京师大学堂地位很高,由朝廷特派的管学大臣管理。管学大臣就是京师大学堂的校长。当时的管学大臣换了几次人,当我进北京大学的时候,学生中正传说管学大臣张百熙的事迹。他可以说是在蔡元培以前的对于北京大学有贡献的一位校长。据说,他当了管学大臣以后,就请吴汝纶为总教习。当时新式学校的教师都称为教习。总教习就是教习的领导。我不知道总教习的职务有什么明文规定,据我推测,他不相当于后来大学中的教务长,教务长的职务主要是管教务行政,而总教习的职务大概是管大学中的学术方面的事。用现在的话说,可能是分工负责学术研究方面的副校长,即管业务的副校长。
吴汝纶是当时著名的桐城派古文家,是当时所谓旧学中的一个权威,但也懂得一点当时所谓新学。严复所翻译的书,有几部都有他作的序。在当时他被认为是一个兼通新旧、融合中西的人物。他在直隶(今河北)做官,在地方上也办了些新式的学校。张百熙要请他当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这就表明了他的办学方针。据说张百熙当了管学大臣以后,亲自到吴汝纶家里去请他出来,吴汝纶都不见。有一天,张百熙在大清早上,穿着管学大臣的公服,站在吴汝纶的卧房门外(有的说是跪在房门外),等吴汝纶起床相见。吴汝纶只好答应他的邀请,但是附带了一个条件,就是他要先到日本去考察几个月,回来后才能到任。张百熙答应了这个条件。吴汝纶从日本回来以后,不久就逝世了,没有来得及到北京大学到任。虽然没有到任,但是这个经过当时传为美谈。当时我们学生听了,也都很感动。感动的是:一方面,张百熙礼贤下士、为学校聘请名师的精神;一方面,吴汝纶对于职务负责、认真学习的精神。正是这种叫学生感动的精神,才是办学校的真正动力。
中华民国成立,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以严复为第一任校长,不过为时不久,后来又换了些人。我于1915年进北大的时候,没有校长,由工科学长胡仁源兼代校长。当时的文科学长是夏锡祺。当时的学系称为“门”。各系没有设系主任,系务由学长直接主持。原来京师大学堂的经科已废,原来经科的课程,有些废止了,有些分配到文科各门中。文科有四个门,即中国哲学、中国文学、中国历史和英文四个学门、我入的是中国哲学门。在我们这个年级以前,还有一个年级。
在1915年9月初,我到北京大学参加开学典礼。由胡仁源主持会场,他作了一个简短的开幕词以后,当时的英文门教授辜鸿铭(汤生)也坐在主席台上,就站起来发言。我不知道这是预先安排好的,还是他自己临时冲动。他的发言很长,感情也很激动,主要的是骂当时的政府和一些社会上的新事物。他是从右的方面反对当时政府的。他说,现在做官的人,都是为了保持他们的饭碗。接着说,他们的饭碗,可跟咱们的饭碗不同,他们的饭碗大得很,里边可以装汽车、姨太太。又说,现在人做文章都不通,他们所用的名词就不通,譬如说“改良”吧,以前的人都说“从良”,没有说“改良”,你既然已经是“良”了,你还“改”什么?你要改“良”为“娼”吗?他大概讲了一个钟头,都是这一类的谩骂之辞。他讲了以后,也没有别人发言,就散会了。当时民国已经成立四年了,辜鸿铭还是带着辫子。开学了,他还是带着辫子来上课。我没有去旁听过他的课,只听到英文门的同学们说,他在堂上有的时候也乱发议论,拥护君主制度。有一次他说,现在社会大乱,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君主。他说,比如说法律吧,你要说“法律”(说的时候小声),没有人害怕;你要说“王法”(大声,一拍桌子),大家就害怕了,少了那个“王”字就不行。总之,凡是封建的东西,他认为都是好的。我听有人说,辜鸿铭在一个地方辩论婚姻制度问题,他赞成一夫多妻制。他说,现在我们这个桌子上一个茶壶带四个茶杯,用着很方便;要是一个茶杯带四个茶壶,那就不像话了。他又说,你们说,西洋人是一夫一妻,不娶姨太太;其实他们每坐一次公共汽车就娶个姨太太。
当时中国文学门的名教授是黄侃(季刚)。在当时的文学界中,桐城派古文已经不行时了,代之而起的是章太炎一派的魏晋文(也可以称为“文选派”,不过和真正的“文选派”还是不同,因为他们不作四六骈体)。黄侃自命为风流人物,玩世不恭,在当时及后来的北大学生中传说着他的佚闻佚事,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比如说,他在北京住在吴承仕(简斋)的一所房子中,他们都是章太炎的学生,本来是很好的朋友。后来不知怎么样闹翻了,吴承仕叫他搬家。黄侃在搬家的时候,爬到房子的梁上写了一行大字:“天下第一凶宅”。
又比如说,他在堂上讲书,讲到一个要紧的地方,他就说:“这里有个秘密,专靠北大这几百块钱的薪水,我还不能讲,你们要叫我讲,得另外请我吃饭。”又比方说,黄侃有个学生,在“同和居”请客,他听见黄侃在隔壁一个房间说话,原来黄侃也在隔壁请客。这个学生就赶紧过去问好,不料黄侃就抓住他批评起来,批评越来越多,这个学生所请的客已经在隔壁房间到齐了,黄侃还不让这个学生走。这个学生心生一计,就把饭馆的人叫来交代说:“今天黄先生在这里请客,无论花多少钱都上在我的账上。”黄侃一听说,就对那个学生说:“好了,你就走吧。”
在我们中国哲学门里,有一位受同学们尊敬的教授,叫陈黼宸(介石),他给我们讲中国哲学史、诸子哲学,还在中国历史门讲中国通史。据说,他是继承浙江永嘉学派的人,讲历史为韩惋胄翻案。他说,到了南宋末年,一般人都忘记了君父之仇,只有韩惋胄还想到北伐,恢复失地。他讲的是温州那一带的土话,一般人都听不懂,连浙江人也听不懂。他就以笔代口,先把讲稿印出来,当时称为发讲义。他上课的时候,登上讲台,一言不发,就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写得非常快,学生们抄都来不及。下堂铃一响,他把粉笔一扔就走了。妙在他写的跟讲义上所写的,虽然大意相同,但是各成一套,不相重复,而且在下课铃响的时候,他恰好写到一个段落。最难得的,是他有一番诚恳之意,溢于颜色,学生感觉到,他虽不说话,却是诚心诚意地为学生讲课。真是像《庄子》所说的“目击而道存矣”的那种情况,说话倒成为多余的了。他的课我们上了一年,到1916年暑假后我再回到北大的时候,听说他已经病逝,同学们都很悲伤。
马叙伦(夷初)给我们开了一门课,叫“宋学”。上了一个学期,他因为反对袁世凯称帝,辞职回南方去了。临行时哲学门的学生开会送行,照了一张相片,他在相片上写了长篇题词。
文科学长夏锡祺不知在什么地方请了一位先生来接替马夷初。那时候,对于教师的考验,是看他能不能发讲义,以及讲义有什么内容。这位先生名不见经传,上课前又没发讲义,我们这班学生对他就有点怀疑了。过了好几天,才发出三页讲义。其中有一个命题是“水为万物之源”。我们这班同学一看,就说这不像一个现代的人所说的话。那时候我当班长,同班的叫我去找学长,说这位先生不行,请换人。学长说:“你们说他不行,总得有个证据呀。”我说他的讲义就是证据。学长说:“讲义怎样讲错了,也得有个理由。”我回到班里一说,同班们每个人都写出几条理由。他的讲义只有油印的三页,我们一下子就写了十几条理由,可以说把他的讲义批得体无完肤。我送给学长。学长一看,也无话可说,只问:“这都是你们自己写的吗?”我说是我们自己写的。学长说:“等我再看看,不过有一条:你们不许跟这位先生直接说什么话或有什么表示,事情由学校解决。”过了一两个星期,没有下文,只有当时的一个学监把我找去,对我说:“某某先生讲义上的错误,你们可以当堂和他辩论。”我说:“学长讲过,不许我们对他直接有所表示。”那位学监说:“彼一时此一时也。”我了解他的意思,大概是学校讽令他辞职,他不肯,所以就让学生直接对付他。等他下一次来上课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带了几本《宋元学案》,在堂上质问,原来他连《宋元学案》都没有见过。同学们哈哈大笑,他狼狈而去。
1916年底,蔡元培来北大担任校长。他是清朝的翰林,后来弃官不做,到德国去留学,通德文,翻译了一些书。用“兼通新旧,融合中西”这个标准说,他在学术界的地位是吴汝纶所不能比拟的。辛亥前后,他也奔走革命。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在南京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孙中山让位后,蔡元培又担任南京临时参议院的代表,来北京催促袁世凯到南京就职。他的政治上的地位,也是很高的。他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社会上无论哪个方面,都认为是最合适的人选。他到校后,没有开会发表演说,也没有发表什么文告,宣传他的办学宗旨和方针。只发了一个布告,发表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就这几个字,学生们全明白了,什么话也用不着说了。
他从德国回来的时候,立了三个原则,以约束自己。这三个原则是:一不做官,二不纳妾,三不打麻将。当时称为“三不主义”。北京大学校长也是由政府任命,但他认为这是办教育,不是做官。其余两条,都是针对着当时社会上的腐化现象而发的,参看上面所说的辜鸿铭的言论,就可知了。
我在北大当学生的时候,只到蔡元培的校长室去过两次。
那时我的弟弟景兰在北京大学预科上学,河南省政府招考留学生,他要往开封去应考,需要一张北京大学的肄业证明书。
时间紧迫,照普通的手续,已经来不及了。我写了一封信,直接跑到校长室。校长室是单独一所房子,设在景山东街校舍的一个旧式院子里。门口也没有传达的人,我就推门进去,房子里中间挂了一个大幔子,我掀开幔子,看见蔡元培正坐在办公桌后面看文件。我走上去,他欠了一欠身,问有什么事。
我把信交给他,他看了,笑笑说:“好哇,好哇,能够出去看看好哇。”我说:“那就请校长批几个字吧。”他提起笔来就写了两个字:“照发”。我拿着他的批示到文书科,看着他们办好证明书,我拿着证明书就走了。
那时候,章士钊(行严)在北大,给一年级讲逻辑。我去旁听过两次。他原来讲的并不是逻辑,而是中国哲学史——墨经。我有几个问题,写信给章士钊,请他解答。他回我一封信,叫我在某一天晚上到校长办公室等他。我按时到了校长室,他还没有到。我坐在幔子外边等他。又陆陆续续来了些人,像是要开什么会的样子。最后,章士钊到了,他那时候年纪还比较轻,穿的也很讲究,很有一点风神潇洒的样子。
他看见我,同我说了几句话,也没有解答问题。我看要开会,就退出来了。
以后我一直没有看见过蔡元培,因为他也不经常露面。一直到1921年,我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他到美国访问,到了纽约。北大的同学组织了一个随从班子,轮流着陪同他到各地方去。有几天,我们常在一起。有一天,在旅馆里,每人都拿出一张纸,请他写字。我恰好有一把折扇,也请他写。
他给每人都写了几句,各不相同。又一天晚上,在纽约的中国学生开会欢迎他,人到的很多。蔡元培一进会场,所有的人都不约而同地站起来了,好像有人在那里指挥一样。有一个久在北京教育界工作的留学生杨荫榆说:“我在中国教育界多年,还没有看见校长和学生间的关系这样好的。北大的学生向来自命甚高,可是见了老校长,这样地恭敬,我现在真是佩服蔡先生了。”
我在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听过蔡元培的讲话,也没有看见他和哪个学生有私人接触。他所以得到学生们的爱戴,完全是人格的感召。道学家们讲究“气象”,譬如说周敦颐的气象如“光风霁月”。又如程颐为程颢写的《行状》,说程颢“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宽而有制,和而不流,……视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阳之温;听其言,其入人也如时雨之润。胸怀洞然,彻视无间,测其蕴,则浩乎若沧溟之无际;极其德,美言盖不足以形容”。(《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一)这几句话,对于蔡元培完全适用。这绝不是夸张。我在第一次进到北大校长室的时候,觉得满屋子都是这种气象。
我有一个北大同学,在开封当了几十年中学校长。他对我说:“别人都说中学难办,学生不讲理,最难对付。这话不对。其实学生是最通情达理的。当校长的只要能请来好教师,能够满足学生求知识的欲望,他们就满意了。什么问题都不会有。”他的这番话,确实是经验之谈。学校的任务基本上是传授知识,大学尤其是如此。一个大学应该是各种学术权威集中的地方,只要是世界上已有的学问,不管它什么科,一个大学里面都应该有些权威学者,能够解答这种学科的问题。
大学应该是国家的知识库,民族的智囊团。学校是一个“尚贤”的地方,谁有知识,谁就在某一范围内有发言权,他就应该受到尊重。《礼记·学记》说:“师严然后道尊”,所尊的是他讲的那门学问,并不是那某一个人。在十年动乱时期,人们把这句话误说为“师道尊严”,其实应该是说“师严道尊”。
张百熙、蔡元培深深懂得办教育的这个基本原则,他们接受了校长职务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为学生选择名师。他们也知道,当时的学术界中,谁是有代表性的人物。先把这些人物请来,他们会把别的人物都召集来。张百熙选中了吴汝纶。蔡元培选中了陈独秀。吴汝纶死得早了,没有表现出来他可能有的成绩。而陈独秀则是充分表现了的。
陈独秀到北大,专当学长,没有开课,也没有开过什么会,发表过什么演说,可以说没有和学生们正式见过面。只有一个故事,算是我们这一班同他有过接触。在我们毕业的时候,师生在一起照了一个相,老师们坐在前一排,学生们站在后边。陈独秀恰好和梁漱溟坐在一起。梁漱溟很谨慎,把脚收在椅子下面;陈独秀很豪放,把脚一直伸到梁漱溟的前面。相片出来以后,我们的班长孙本文给他送去了一张,他一看,说:“照得很好,就是梁先生的脚伸得太远一点。”孙本文说:“这是你的脚。”这可以说明陈独秀的气象是豪放。
附带再说两点。陈独秀的旧诗做得不错。邓以蛰(叔存)跟他是世交,曾经对我说,陈独秀作过几首游仙诗,其中有一联是:
九天珠玉盈怀袖,万里仙音响佩环。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重庆碰见沈尹默,谈起书法。沈尹默说,还是在五四运动以前,陈独秀在他的一个朋友家里,看见沈尹默写的字,批评说:“这个人的字,其俗在骨,是无可救药的了。”沈尹默说,他听了这个批评以后,就更加发奋写字。从“其俗在骨”这四个字,可以看出陈独秀对于书法评论的标准,不在于用笔、用墨、布局等技术问题,而在于气韵的雅俗。如果气韵雅,虽然技术方面还有些问题,那是可以救药的。如果气韵俗,即使在技术方面没有问题,也不是好书法,而且这些弊病是不可救药的。书法的好坏,主要是在于气韵的雅俗。从“在骨”两个字,可以看出陈独秀评论书法,也不注重书法的形态,而注重形态所表现的那些东西。
这是他对于书法理论的根本思想,也是他对于一切文艺理论的根本思想。这是他的美学思想。
以上所说的,大概就是在十年大动乱中所批判的所谓“智育第一”“学术至上”吧。“学术至上”一经受到批判,就一变而为“学术至下”了。“知识越多越反动”,成了一条“规律”。很有些像在农村中,谁要富起来,谁就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越富越修”,也成了一条“规律”。当时有人在农村提倡“穷过渡”。在学校中所提倡的,可以说是“愚过渡”。
好像非穷非愚,就不能过渡到共产主义。实践已经证明,这种极左思潮的危害性是多么大了。
随着“学术至上”而受到批判的是“为学术而学术”。历史唯物主义者应该知道,“为学术而学术”这个口号在当时是针对什么而说的,它所针对的是“为做官而学术”。上面已经说过,在清末民初时代,人们还是把学校教育当成为变相的科举。哪一级的学校毕业,等于哪一级的科举功名,人们都有一个算盘。上学校为的是得文凭。得了哪一级学校的文凭,就等于得了哪一级的科举功名。学术成了一种做官向上爬的梯子。蔡元培的“三不主义”中,首先提出“不做官”,就是针对着这种思想而发的。他当了北大校长以后,虽然没有开会宣传“不做官”的原则,但从他的用人开课这些措施中间,学生们逐渐懂得了,原来北京大学毕业并不等于科举时代的进士;学术并不是做官向上爬的梯子,学术就是学术。为什么研究学术呢?一不是为做官,二不是为发财,为的是求真理,这就叫“为学术而学术”。学生们逐渐知道,古今中外在学术界有所贡献的人们,都是这样的人们。就中国的历史说,那些在学术界有所贡献的人们,都是在做官的余暇做学问的。
他们都可以说是业余的学问家,学问的爱好者。虽然是业余,可是成功以后,他们的成绩也还是对于国家、人民和人类大有好处的。学问这种东西也很怪,你若是有所为而求它,大概是不能得到它。你若是无所为而求它,它倒是自己来了。作为业余的学术爱好者,为学术而学术尚且可以得到成绩,有所贡献。如果有人能够把为学术而学术作为本业,那他的成绩必定更好,贡献必定更大。
在十年大动乱时期,还批判了所谓“教授治校”。这也是蔡元培到北大后所推行的措施之一。其目的也是调动教授们的积极性,叫他们在大学中有当家作主的主人翁之感。当时的具体办法之一,是民主选举教务长。照当时的制度,校长之下,有两个长:一个是总务长,管理学校的一般行政事务;一个是教务长,管理教学科研方面的事务。蔡元培规定,教务长由教授选举,每两年改选一次。我在北大的时候,以学生的地位,还不很了解所谓“教授治校”究竟是怎么个治法。
后来到了清华,以教授的地位,才进一步了解所谓“教授治校”的精神。这一点以下再说。
教授之所以为教授,在于他在学术上有所贡献,在他本行中是个权威,并不在于他在政治上有什么主张。譬如辜鸿铭在民国已经成立了几年之后,还是带着辫子,穿着清朝衣冠,公开主张帝制,但是他的英文在当时说是水平很高的,他可以教英文,北大就请他教英文,在蔡元培到校以前就是事实。蔡元培到校,也没有改变这个事实,他还又加聘了一个反动人物,那就是刘师培(申叔)。刘师培出身于一个讲汉学的旧家,在清朝末年他在日本留学,说是留学,实际上是在东京讲中国学问。那时候,在东京这样的人不少,章太炎也是其中的一个。当时在东京这样的人中,比较年轻的都以章太炎为师,刘师培却是独立讲学的。这样的人也都受孙中山的影响,大多数赞成同盟会。刘师培也是如此。袁世凯在计划篡国称帝的时候,为了制造舆论,办了一个“筹安会”,宣传只有实行帝制才可以使中国转危为安。筹安会有六个发起人,当时被讥讽地称为“六君子”。在六人之中,学术界有两个知名人士,一个是严复,一个是刘师培。在袁世凯被推翻以后,这六个人都成了大反动派。就是在这个时候,蔡元培聘请刘师培为中国文学教授,开的课是中国中古文学史。我也去听过一次讲,当时觉得他的水平确实高,像个老教授的样子,虽然他当时还是中年。他上课既不带书,也不带卡片,随便谈起来,就头头是道。援引资料,都是随口背诵。当时学生都很佩服。他没有上几课,就病逝了。
这就是所谓“兼容并包”。在十年大动乱的时候,这也是一个批判的对象。所谓“兼容并包”,在一个过渡时期,可能是为旧的东西保留地盘,也可能是为新的东西开辟道路。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在当时是为新的东西开辟道路的。
那个时候的北大,用一个褒义的名词说,是一个“自由王国”;用一个贬义的名词说,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王国”。在蔡元培到北大以前,各学门的功课表都订得很死。既然有一个死的功课表,就得拉着教师讲没有准备的课,甚至他不愿意讲的课。后来,选修课加多了,功课表就活了。学生各人有各人的功课表。说是选修课也不很恰当,因为这些课并不是有一个预订的表,然后拉着教师们去讲,而是让教师们说出他们的研究题目,就把这个题目作为一门课。对于教师们说,功课表真是活了。他所教的课,就是他的研究题目,他可以随时把他研究的新成就充实到课程的内容里去,也可以用在讲课时所发现的问题发展他的研究。讲课就是发表他的研究的机会,研究就是充实他的教学的内容。这样,他讲起来就觉得心情舒畅,不以讲课为负担;学生听起来也觉得生动活泼,不以听课为负担。这样,就把研究和教学统一起来了。说“统一”,还是多了两个字,其实它们本来就是一回事。有一位讲公羊春秋的老先生崔适,他写了一部书,叫《春秋复始》,并且已经刻成木板,印成书了。蔡元培把他请来,给我们这一班开课,他不能有系统地讲今文经学,也不能有系统地讲公羊春秋,只能照着他的书讲他的研究成果。
好,你就讲你的《春秋复始》吧。他上课,就抱着他的书,一个字一个字地念。我们当时的水平,也提不出什么问题。他就是那么诚诚恳恳地念,我们也恭恭敬敬地听。开什么课,这是教师的自由,至于这个课怎么讲,那更是他的自由了。你可以说韩惋胄好,我可以说韩惋胄坏,完全可以唱对台戏。
戏可以唱对台戏,为什么学术上不可以对堂讲呢。至于学生们,那就更自由了。他可以上本系的课,也可以上别系的课。你上什么课,不上什么课,没人管;你上课不上课也没人管。只到考试的时候你去参加考试就行。如果你不打算要毕业证书,就不去参加考试,也没人管。学校对于校外群众也是公开的。
学校四门大开,上课铃一响,谁愿意来听课,都可以到教室门口要一份讲义,进去坐下就听。发讲义的人,也不管你是谁,只要向他要,他就发,发完为止。当时有一种说法,说北大有三种学生,一种是正式学生,是经过入学考试进来的;一种是旁听生,虽然没有经过入学考试,可是办了旁听手续,得到许可的;还有一种是偷听生,既没有经过入学考试,也不办旁听手续,不要许可,自由来校听讲的。有些人在北大附近租了房子,长期住下当偷听生。
在这种情况下,旁听生和偷听生中可能有些是一本正经上课的,而正式中有些人上课不上课就很随便。当时有一种说法,到八大胡同(当时北京妓院集中的地方)去的人,比较多的是两院一堂。两院指的是当时的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一堂指的是北京大学(当时沿称大学堂)。北大的这种情况,从蔡元培到校后已经改得多了,但仍有其人。有些学生在不上课的时候,也并非全干坏事。顾颉刚告诉我说,他在北大当学生的时候,喜欢看戏。每天在上午第二节课下课的时候,他就走出校门,到大街上看各戏园贴出的海报。老北京的人把看戏说成“听”戏。在行的人,在戏园里,名演员一登场,他就闭上眼睛,用手指头轻轻地打着拍子,静听唱腔。只有不在行的人才睁开眼睛,看演员的扮相,看武打,看热闹。顾颉刚是既不听,也不看,他所感到兴趣的是戏中的故事。同是一个故事,许多戏种中都有,不过细节不同。看得多了,他发现一个规律:某一出戏,越是晚出,它演的那个故事就越详细,枝节越多,内容越丰富。故事就好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由此他想到,古史也有这种情况。故事是人编出来的,经过编的人的手越多,内容就越丰富。古史可能也有写历史的人编造的部分,经过写历史的人的手,就有添油加醋的地方,经的手越多,添油加醋的地方也越多。这是他的《古史辨》的基本思想,这个思想,是他从看戏中得来的。
照上边所说的,北大当时的情况,似乎是乱七八糟,学生的思想,应该是一片混乱、派别分歧,莫衷一是。其实并不是那个样子,像上边所说的,辜鸿铭、刘师培、黄侃等人的言论行动,同学们都传为笑谈。传说的人是当成笑话说的,听的人也是当成笑话听的,所谓“兼容并包”不过是为几个个人保留领薪水的地方,说不上保留他们的影响。除了他们的业务外,他们也没有什么影响之可言。为新事物开辟的道路,可是越来越宽阔,积极的影响越来越大。陈独秀当了文科学长以后,除了引进许多进步教授之外,还把他在上海办的《新青年》杂志,搬到北京,成为北大进步教授发表言论的园地。学生们也写作了各种各样的文章,在校外报刊上发表。学生们还办了三个大型刊物,代表左、中、右三派。左派的刊物叫《新潮》,中派的刊物叫《国民》,右派的刊物叫《国故》。这些刊物都是由学生自己写稿、自己编辑、自己筹款印刷、自己发行,面向全国,影响全国。派别是有的,但是只有文斗,没有武斗。
上边所引的那位中学校长说,学生是通情达理的,不仅通情达理,就是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他们的判断水平也是不能低估的。当时已经是五四运动的前夕,新文化运动将达到高潮,真是人才辈出,百花争艳,可以说是“汉之得人,于斯为盛”。
就是这些人,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就是这些人,采取了外抗强敌、内除国贼的行动。在中国历史中,类似的行动,在太学生中是不乏先例的。这是中国古代太学的传统。五四运动继承并且发扬了这个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