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笔记产生不了学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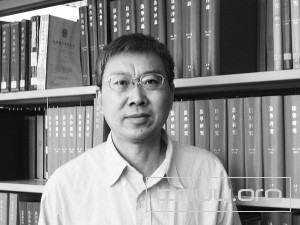
如果说美国大学课堂的特点是讨论多,那么中国课堂的普遍景象便是记笔记。在21世纪的今天,学生先记后背,以此道来求学问,其实是基于一种过时了的,文艺复兴时期的知识观。福柯(MichelFoucault)在《事物的秩序:人文科学考古学》一书中说,文艺复兴后期处在一个"知识观"从"注释"向"评说"转型的时代。"注释"的任务主要是搜集,然后才是添加,对任何一种对象或话题,不管是由谁写的,只要把前人写过的所有东西尽量收集起来,就能合为一个知识整体。"评说"则不同,它需要求知者从自己的观察和判断出发,就前人或别人说过的话或积累的知识作评价性的甄别,在其中选择那些与自己求知目的相一致的部分。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教学以分析和记诵古典文本为主,用"记笔记"的方法来积累"注释"型的知识。人文主义教育家维夫斯(JuanLuisVives,1493-1540)曾这样介绍这个学习方法:"用适当大小的空白页钉一个本子,将这个本子分成一些标题(topics),形成一组一组要记录的内容。例如一组可以用来记下日常说话的'话题名称',如心灵、身体、职业、游戏、衣服、时间区分、住所、食物。另一组可以用来记下'惯用法';再一组可以记下句子;另一组记'成语';又一组记'作家所写的较难的段落';再一组记'你自己或你的教师认为值得记住的东西'。"
将"笔记本和标题"推向极致并产生极大影响的是基督教人文学者伊拉斯谟(Erasmus,1466-1536)。他在《论词语的丰富》中对这个方法的运用要比维夫斯系统得多,而且也更能体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知识观念。这部著作在伊拉斯谟活着的时候至少发行了85版。
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者们把知识的积累当做知识的主要目的,至于积累的知识是否真实、可靠,则不太为人所在意。因此,确实的知识和道听途说的"知识"往往混杂在一起。如果一个人能用许多不同的方式表达同一个意思(不必是他自己的意思),那他就是一个知识丰富、学问渊博的人。《论词语的丰富》就是一部这样的知识渊博之书。书题的简称DeCopia的意思是"丰饶"、"丰富"。知识丰富的人才会"能说会道",能说会道不只是口齿伶俐,而且是对什么都有话可说,对任何话题都可滔滔不绝。人文主义者把知识全面当做渊博,同时还要求善于用文字言辞表达知识,因此,写作的能力也就格外重要。
在伊拉斯谟那里,知识的丰富分为三个部分,第一是丰富的词汇(copiaverborum),如果用了一个字或词以后,还能用其他不同的说法来代替它,那就算是词汇丰富、表述多样。但是,伊拉斯谟认为,只有词汇还不足以使一个人雄辩,所以还要具有第二种丰富:丰富的修辞手段(copiarerum)。他列举了各种可以用来说明一个意思的手段,如隐喻、提喻、类比、寓言、虚构故事、警句、格言、箴言,就是说,为了增加说服力,需要使用多种说明手段。第三种丰富是话题和题材。他举例说,同一件事情可以用来说明不同的道理,得出不同的结论,所以一个写作者应当小心使用自己的例子。例如,苏格拉底在受审时被人以不真的指控害死。这个事情可以用来说明"真理招人憎恨",但它也可以用来说明"不凡的美德招人嫉妒"或者"法官裁判不考虑受审者是否优秀"。
《论词语的丰富》的那种人文教育其实只适用于极少数的人文学者,作为一种普遍的教学方法,它在一般学校里的效果与原来的设计有很大的距离。学生往往只是机械模仿,学到一点皮毛而已。但它却为我们揭示了人文主义教育复兴古典的一些基本特征。首先,它采用的是"分析"的方法,也就是把"整体"(阅读的文本)化为"部分"(用标题和小标题的办法记下阅读到的东西)。这种分析取决于阅读者自己的"分类"意识和方法,这本身就是一种消化的结果。
第二,仅仅分类或分析还不够,那只是第一步,第二步是记忆,在脑子里记住自己记在笔记本里的东西。记忆一直是传统教育的一个重要方法。把希腊和罗马文学拆散成为"笔记",为的是使这些古典化为许多便于记忆或在运用中可以重复的现成材料。这当然是一个极大的工程,令人想起钱钟书的《管锥篇》,而尤其令我们赞叹的是他们的记忆功夫。当时有专门传授记忆技能的。例如,教学生在头脑里想象面前有一道长墙,墙顺次分成8段,每一段都写着需要记住的东西。学生每天早晨一醒过来,就要设想自己站在这长墙前,一段一段地依次在读墙上写着的东西。
记忆的要诀是记住许多孤立的东西,然后再按照自己的需要,把它们重新组合,这曾经是高等教育所追求的聪明才智。今天,这种聪明才智的重要性已经被独立思考和价值判断所代替。文艺复兴时期的观念已经离我们今天的知识观和人才观非常遥远。在欧洲,这种知识观的影响只延续到17、18世纪,到启蒙时代后便已彻底改变。
